作者:樂倚萍
讀來不「憂鬱」
憂鬱是種病嗎?倘說它是病,為何那些帶有憂鬱氣質的名人有著難以名狀的魅力?為何偉大的藝術家在憂鬱中獲得靈感?為安在特定的時期人們競相以憂鬱為榮?倘說它不是病,為何古往今來研究它最甚的是醫生?為何它給患者及家屬帶來身心的折磨?為何某些藥物似乎能緩解症狀?
我們彷徨無措,不知何以解憂。美國作家克拉克·勞勒追本溯源,或能令人看得真切。克拉克·勞勒任教於諾森比亞大學英國文學系,熱衷於疾病文化史的研究,已出版《憂鬱症之前》《肺病與文學:浪漫的疾病》等歷史著作。
《從犯愁到解愁:憂鬱症的歷史》講述了不同時代人們和憂鬱之間的關係。其中不乏我們耳熟能詳的主人公:古羅馬的蓋倫、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們、莎翁筆下的哈姆雷特、博學多識的《英語大辭典》作者塞繆爾·約翰遜、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勞勒帶我們用已知的片段串聯起未知的領域,即便介紹醫學研究的專業知識,讀來也絕不「憂鬱」。
曾經,因為亞裡士多德模式美化了憂鬱症,男男女女都願意跟別人宣稱,自己至少帶有那麼一絲憂鬱的氣質,或者說「脾性」。這個病雖然是從義大利開始流行的,但很快,它就通過歐洲的知識分子和貴族網路傳播到了北部地區,最終在英國深深地紮下了根。於是,哈姆雷特這樣的文學形象誕生了。這種形象又進一步形成了刻板模式,不久之後,描寫憂鬱青年的諷刺文字也出現了。哈姆雷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黑色諷刺的對象。到了1580年左右,有這樣一個群體得到了社會的承認。他們是憂鬱的「反叛分子」,心懷抱負,想努力地向上攀爬,但因為世道艱難,遭遇了很多挫折,心裡也很不滿。這類人基本上都覺得,自己就算不是天才,也是很有才華的。
探索「解憂」之道
本書提供了一個獨特而有見地的敘述,記錄了人類在定義和治療憂鬱症方面古今變遷的歷史。例如,在古希臘,人們認為喝太多深色的烈酒,吃大量陳年的奶酪,將使黑膽汁(憂鬱體液)分泌過多,引發憂鬱症;在現代世界,標準化的憂鬱症診療手段推廣,制藥業資本巨頭參與憂鬱症的概念建構,新型憂鬱症被定義,全球憂鬱症患者激增。縱觀歷史,無論人們對憂鬱(或憂鬱)的認知如何,都在探索「解憂」之道。
有些方法如今看來怪誕無稽,對照當時人們對病因的歸納卻也是「對症下藥」。譬如,根據古希臘人的「體液說」,「憂鬱症」的疾病肇因被認為是體內黑膽汁過多。解決方法便是清除黑膽汁,無論是放血、水蛭療法,還是服用有毒的嚏根草催吐催瀉,都是達成目的的手段。18世紀的英國醫生喬治·切恩算是那個年代的「網紅」,他很擅長跟不懂醫學的人交流,自稱治好了自己的憂鬱症,也是他美其名曰「英國病」,將症結歸咎於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導致的貪婪和神經纖弱,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患病。切恩強調,吃素戒酒、調理腸胃,輔之以體育鍛煉,是治療「英國病」的良方,這些不成其為治療方法的方法令其聲名大噪。憂鬱症不只是個人問題,也有社會性原因,19世紀的精神療法頗具人文色彩,友善陪伴患者,傾聽並安慰。但勸說未必總是有效,分析憂鬱症患者的精神世界逐漸成為一件專業的事。
今天我們如何治療憂鬱症?無論身邊有沒有患者,大多數人都能像報出感冒藥、腹瀉藥的名稱一樣,熟稔地報出「百憂解」,這實在是制藥公司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百憂解和抗憂鬱藥的普及是上世紀末的事。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手冊》第三版問世,「成為新型憂鬱症的《聖經》」,不同醫生按圖索驥,也可根據症狀給出相同的診斷,那麼開出相同的藥方亦順理成章。而相比前人放血、電擊、額葉切除之類的激進療法,吃藥更易被接受,聽起來也更有現代科學的依據。於是,抗憂鬱藥物銷量攀升,似乎是對抗情緒問題的解藥。
對此,早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一方面,《手冊》中的評估標準不算完善,一個正常人遭遇重大變故或壓力時,也極可能產生《手冊》中的症狀,未必需要立即糾正。另一方面,藥物的效果也飽受質疑,有些研究者認為,它們並不比安慰劑更有效,遑論藥物被濫用的風險。歸根到底,我們對憂鬱症的了解依然很膚淺,甚至充滿主觀色彩。
憂鬱症也有文化脈絡
值得一提的是,《從犯愁到解愁:憂鬱症的歷史》引用大量資料,探究憂鬱症在文學藝術作品中的表現,視角獨特地呈現了憂鬱症的文化史脈絡。例如,18世紀末的哥特式文學和憂鬱症之間是有聯絡的,墓園派詩歌就是從憂鬱症裡汲取了靈感;從莎士比亞創作的經典人物形象哈姆雷特的憂鬱性格裡,我們能看到亞裡士多德、柏拉圖、費奇諾、蓋倫、占星術、人文主義、煉金術的各種理念。
生活在不同時代,人們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和壓力,產生憂鬱雖有身體的原因,更有社會的因素,後者可能不易被其他群體承認。拿今日常見的產後憂鬱來說,父輩們初為父母時,難道不曾有過艱難歲月嗎?他們很難理解物質條件更優渥的當代父母如何身心脆弱,但這顯然不能單純以心理素質作結。解憂應當雙管齊下,對效率的追逐讓我們傾向於簡化問題——交給藥物,而忽略駐足傾聽旁人的聲音,予以共情和關懷。嘗試化解個人的憂鬱,亦是在為撫平社會的憂傷貢獻涓滴之力。(樂倚萍)
來源: 解放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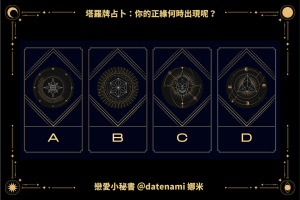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