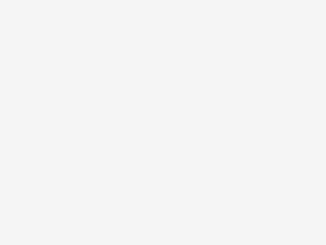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施一公,中國科學院院士、結構生物學家、清華大學教授。1967年5月5日出生於河南省鄭州,198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95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
主要從事細胞凋亡及膜蛋白兩個領域的研究。在Smad對TGF-的調控機理、磷酸酶PP2A的結構生物學方面做出過有國際影響的工作。曾獲國際賽克勒生物物理學獎、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傑出科學家獎、談家楨生命科學終身成就獎、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2014年度愛明諾夫獎等獎項。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外籍成員。

(一)所有成功的科學家一定具有的共同點,就是他們必須付出大量的時間和心血。這是一條真理。實際上,無論社會上哪一種職業,要想成為本行業中的佼佼者,都必須付出比常人多的時間。
大約10年前,著名華人生物學家蒲慕明先生曾經有一封郵件在網上廣為流傳,這封郵件是蒲先生語重心長寫給自己實驗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後的,其中的觀點我完全讚同。無論是在普林斯頓還是在清華大學,我都把這封郵件轉PO給實驗室的所有學生,讓他們體會。其中的一段是這樣說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實驗室里的工作時間,當今一個成功的年輕科學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時左右的時間投入到實驗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議每個人每天至少有6小時投入緊張的實驗操作,並且用兩小時以上的時間從事與科研直接相關的閱讀等工作。文獻和書籍的閱讀則應主要在這些工作時間之外進行。」
有些學生讀完郵件後告訴我:「看來我不是做學術的料,因為我真的吃不起這份苦。」我常常回復道:「我在你這麼大年紀的時候,也會覺得長期這樣工作不可思議。但在不知不覺中,你會逐漸被科學研究的精妙所打動,也會為自己的努力和成績而驕傲,你會逐漸適應這種生活方式!」這樣的回答,其實源自我自己的經歷與體會。
我從小就特別貪玩,並不喜歡學習,但來自學校和父母的教育與壓力迫使我盡量刻苦讀書。我高中就讀於河南省實驗中學,憑借著比別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綜合成績始終名列前茅。1984年全國高中數學聯賽我獲得河南賽區第一名,保送進入清華大學。大學階段,我保持了刻苦的傳統,綜合成績全班第一並提前一年畢業。然而事實上,我很少真正獨立思考,對所學專業也不感興趣。大學畢業時,我本沒有打算從事科學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經商,結果陰差陽錯間踏上了赴美留學之路。
可想而知,留學的第一年,我情緒波動很大,內心浮躁而迷茫,根本無心念書、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時間在中餐館打工、選修計算機課程。第二年,我開始逐漸適應科研的「枯燥」,並開始有了一點自己的體會,有時領會了一些精妙之處後不免 「洋洋得意」,也會產生「原來不過如此」的想法,逐漸對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點自信。這期間,博士研究生的課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從上午9點做實驗到晚上七八點,周末也會去兩個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經開始領會到科研的邏輯,有點兒躍躍欲試的感覺,在組會上常常提問,而這種「入門」的感覺又讓我對研究增加了很多興趣,晚上常常幹到11點多,趕最後一班校車從霍普金斯醫學院回到住處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區。1993年,我曾經在實驗記錄本的日期旁標註 「這是我連續第21天在實驗室工作」,以此激勵自己。其實,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為其中的一個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個小時的實驗。到第四年以後,我完全適應了實驗室的科研環境,也不會再感到枯燥或時間上的壓力了。時間安排完全服從實驗的需要,盡量往前趕。其實,這段時期的實驗時間遠多於剛剛進實驗室的時候,但感覺上好多了。
研究生階段後期,我的刻苦在實驗室是出了名的。在紐約做博士後時期則是我這輩子最苦的兩年,每天晚上做實驗到半夜3點左右,回到住處躺下來睡覺時常常已是4點以後;但每天早晨8點都會被窗外紐約第一大道上的汽車喧鬧聲吵醒,9點左右又回到實驗室開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實驗室,分別在上午9點、下午3點和晚上九十點。這樣的生活節奏持續11天,從周一到第二個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長途汽車回到巴爾地摩的家里。周末兩天每天睡上近 10個小時,彌補過去11天嚴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開始下一個11天的奮鬥。雖然體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滿足、很驕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動打造未來、在創業,有時也會在日記里鼓勵自己。我住在紐約市曼哈頓區65街與第一大道路口附近,離紐約著名的中央公園很近,那里時有文化娛樂活動,但在紐約工作整整兩年,我從未邁進中央公園一步。
我一定會把自己的這段經歷講給我的每一個學生聽,新生常常問我:「老師,您覺得自己苦嗎?」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沒興趣的事情時覺得很苦,有興趣以後一點也不覺得苦。」是啊,一個精彩的實驗帶給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國大片強多了。現在回想起當時的刻苦,感覺仍然很驕傲、很振奮!有時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後階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進取,而是不加節制地看電影、讀小說、找娛樂(當時的互聯網遠沒有現在這麼內容豐富),現在該是什麼狀況?
做一個優秀的博士生,付出時間是必要條件。
(二)要想在科學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僅僅刻苦地付出時間是不夠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analysis)是必須具備的一種素質。
博士研究生與本科生最大的區別是:本科生以學習吸取人類積累的知識為主,兼顧科學研究和技能訓練;而博士生的本質是通過科學研究來發掘創造新知識,當前和以往學習的知識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科學研究。在以學習知識為主的本科生階段,提出問題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經存在,所以問題是否具有批判性沒有那麼關鍵。博士生階段則完全不同,必須具備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則不可能成為優秀的科學家。這一點,我稱之為方法論的轉變。
其實,整個大學和研究生階段教育的實質就是培養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學生具備能夠進行創新科研的方法論。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蓋的範圍也非常廣,在此擇要舉例說明。
正確分析負面結果(negativeresults)是成功的關鍵。作為生命學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個實驗都很順利、能得到預料中的正面結果(positiveresults),除個別研究領域外,一般只需要6~24個月就應該可以獲得博士學位所需要的所有結果了。然而實際上,在美國,生命學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得到博士學位。這一數字本身就說明:絕大多數實驗結果會與預料不符,或者是負面結果。大多數低年級博士生對負面結果的看法很消極,直接影響了他們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養。
其實,只要有適當的對照實驗,判斷無誤的負面實驗結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一般來說,任何一個探索型課題的每一步進展都有幾種、甚至十幾種可能的途徑,取得進展的過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確路徑、找到正確方向的過程,很多情況下也就是將這幾種、甚至十幾種可能的途徑一一予以嘗試、排除,直到找到一條可行之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可信的(conclusive)負面結果往往可以讓我們信心飽滿地放棄目前這一途徑。如果運用得當,這種排除法會確保我們最終走上正確的實驗途徑。從這個角度講,負面的實驗結果不僅很正常,也很有益於課題的最終成功。我告誡並鼓勵我所有的學生:只要你不斷取得可信的負面結果,你的課題就會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斷分析負面結果的過程中所掌握的強大的邏輯分析能力也會使你很快成熟,成長為一名優秀的科學家。
我對一帆風順、很少取得負面結果的學生總是很擔心,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經歷過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訓練。我的實驗室里偶爾會有這樣的學生,只用很短的時間(兩年左右,有時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論文所需要的結果。對這些學生,我一定會讓他們繼續承擔一些富有挑戰性的新課題,讓他們經受負面結果的磨練。沒有這些磨練,他們很難真正具備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將來也很難成為可以獨立主管一個實驗室的優秀科學家。
所以,不要害怕負面結果,關鍵是如何從分析負面結果的過程中獲取正確的信息。
(三)「一個人必須對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無論閱讀科研文獻還是聆聽學術講座,目的都是為了借鑒相關經驗,更好地服務於自己的科研課題。」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費時間的完美主義阻礙創新進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後導師,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科學家之一。他有極強的實驗判斷力和思維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譽世界結構生物學界,31歲時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剛到尼古拉實驗室不久,純化一個表達量相當高的蛋白 Smad4。兩天下來,蛋白雖然純化了,但結果很不理想:得到的產量可能只有應該得到的20%左右。見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說:「產率很低,我計劃繼續優化蛋白的純化方法,提高產率。」他反問我:「你為什麼想提高產率?已有的蛋白不夠你做初步的結晶實驗嗎?」我「回敬」道:「我有足夠的蛋白做結晶篩選,但我需要優化產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氣地打斷我:「不對。產率夠高了,你的時間比產率重要。請盡快開始結晶。」實踐證明了尼古拉建議的價值。我用僅有的幾毫克蛋白進行結晶試驗,很快意識到這個蛋白長度並不理想,需要通過蛋白質工程除去其N-端較柔性的幾十個氨基酸。事實上,除去N-端幾十個氨基酸的蛋白不僅表達量高,而且生化性質穩定,純化起來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擔心產率的問題。
在大刀闊斧進行創新實驗的初期階段,對每一步實驗的設計當然要盡量仔細。但一旦按計劃開始後,對其中間步驟的實驗結果則不必追求完美,而是應該義無反顧地把實驗一步步推到終點,看看可否得到大致與假設相符的總體結果。如果大體上相符,你才應該回過頭去仔細改進每一步的實驗設計。如果大體不符,而總體實驗設計和操作都沒有錯誤,那你的假設(或總體方向)很可能是有大問題的。
這個方法論在每一天的實驗中都會用到。從1998年開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到現在,我一直告誡所有學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獻與學術講座的取舍
再來談談科研文獻(literature)與學術講座(seminar)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學多才,在我們許多博士後的心目中,他一定讀很多文章、常常去聽學術講座。沒想到,事實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階段,我的導師傑里米·伯格非常重視相關科研文獻的閱讀,每周召開組內文獻討論會,討論重要的科研進展。剛到尼古拉實驗室時,我曾試圖表現一下自己讀文獻的功底,也想同時與尼古拉討論以得到他的「真傳」。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讀了一篇《自然》雜誌的文章,午飯前遇到尼古拉時,我向他描述了這篇文章的精妙,同時期待著他的評述。尼古拉面色有點尷尬:「對不起,我還沒看過這篇文章。」當時我想,噢,也許這篇文章太新,他還沒有來得及讀。過了幾天,我閱讀了一篇幾個月前在《科學》上發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討論,沒想到他又說沒看過。幾次碰壁之後,我不解地問他:「你知識如此淵博,一定是廣泛閱讀了大量文獻,為什麼恰好沒有讀我提到的這幾篇論文呢?」尼古拉看著我說:「我的閱讀並不廣泛。」我反問:「如果你不廣泛閱讀,你的科研成果怎麼會這麼好?你怎麼能在自己的論文里引用這麼多文獻?」尼古拉的回答讓我非常意外:「我只讀與我的研究興趣有直接關係的論文,並且只有在寫論文時我才會大量閱讀。」
我做博士後的單位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學術講座,常常會請來自生命科學各個領域的「大牛」演講。有一次,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來作講座,並且點名要與尼克拉交談。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這可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機會。尼古拉卻告訴他的秘書:「請你替我轉達我的歉意,講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們也為尼古拉感到遺憾。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諾貝爾獎得主演講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從早晨到傍晚一直沒有出門,自然也沒有去聽講座。當然,這也許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計劃。但以我們對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寫論文。後來,我們也意識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經見怪不怪了。
離開尼古拉實驗室前,我向他拋出了這個始終沒有完全解開的謎:「如果你不怎麼讀文獻,又不怎麼去聽講座,你怎麼還能做一個如此出色的科學家?」他回答說,他的時間有限,每天只有10小時左右在實驗室。權衡利弊之後,他只能把有限的時間用在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結構、與學生討論課題或寫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一個人必須對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無論閱讀科研文獻還是聆聽學術講座,目的都是為了借鑒相關經驗,更好地服務於自己的科研課題。
(四)在博士生階段,尤其是前兩年,我認為必須花足夠的時間去聽各相關領域的學術講座並進行科研文獻的廣泛閱讀,打好批判性思維的基礎;但隨著科研課題的深入,選擇文獻閱讀和學術講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針對性,也要開始權衡時間的分配了。
挑戰傳統思維。從我懂事開始,就受到這樣的教育:凡事失敗都有其道理,應該找到失敗的原因後再重新開始嘗試。直到1996年,我在實驗上也遵循這一原則。但在尼古拉的實驗室,這一「基本原則」受到了有理有據的挑戰。
有一次,一個比較複雜的實驗失敗了。我很沮喪,準備花幾天時間多做一些對照實驗找到問題所在。沒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皺著眉頭問我,為什麼要搞明白實驗為何失敗?我覺得這個問題太沒道理,理直氣壯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錯了才能保證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馬上評論說:「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實驗重復一遍,也許下次就可以做成。與其花大把時間搞清楚一個實驗為何失敗,不如先重復一遍。面對一個失敗了的複雜的一次性實驗,最好的辦法就是認認真真重新做一次。」後來,尼古拉又把他的這一觀點作了升華:「是否要弄清楚一個實驗為何失敗,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厘清每一個小差錯的習慣性思維並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細想想,這些話很有道理。並不是所有失敗的實驗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學的實驗。因為實驗過程繁瑣複雜,大部分失敗是由簡單的操作錯誤引起的,可以仔細重新做一遍,這樣往往可以解決問題。只有那些關鍵的、不找到失敗原因就無法前行的實驗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選擇的這些例子多少有點 「極端」,但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蕩大家思維的作用。其實,在我自己的實驗室里,這幾個例子早已經給所有學生反復講過多次了,而且每次講完之後,我都會告訴大家要打破迷信、懷疑成規,關鍵的關鍵是:跟著邏輯走!跟著邏輯走,這是我在實驗室里注定會重復強調的一句話,每天至少要對不同的學生講5遍以上。我自己每次與博士生討論課題也總是遵循嚴密的邏輯,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實驗的下一步解決方案。嚴密的邏輯,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
聲明: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ND·
微信號:keyuanzh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