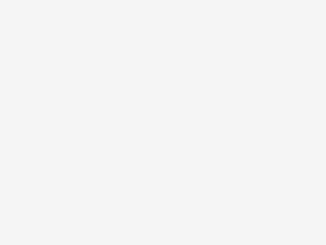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王珮瑜主演京劇《朱砂痣》劇照
餘孟叮當響珮瑜
——評餘派名劇《朱砂痣》
的前世今生
齊致翔
最近從電視看到王珮瑜主演的京劇《朱砂痣》,十分欣賞、感動和欣慰,也引發了筆者對京劇傳統、流派繼承、發展及其時代審美意蘊的思考。
王珮瑜是上海京劇院青年演員,當代炙手可熱的餘派坤生,人稱小冬皇或小孟小冬。其餘派造詣世所公認,粉絲遍布全國。但其依然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績,孜孜以求作為新時代京劇傳統和流派藝術繼承者應有的新的奮發與作為,以適應今天觀眾的期許和要求。近年來,她對京劇以外事務的熱情參與,展現了其活力與潛質。當然,人們更驚訝於她對餘、孟先師的尊崇與追隨。她不僅一段不落地演繹了餘叔巖留下的其在不同時期錄制的全部十八張半唱片,進而將餘大師未及錄制的《朱砂痣》搶救復活,幾年後又做成「像音像」,借現代傳媒唱響大江南北千家萬戶,環珮叮當,美不勝收,對京劇的傳揚做出新的貢獻。
餘承於譚,異於譚,創造了京劇發展史上的奇跡,展現了譚鑫培後老生藝術山不厭高的永續風流,將京劇初始的無生不譚賡續為流傳久遠的譚餘一家、譚餘一脈的無生不餘。在餘的傳習下,其弟子又發展創造出譚富英的新譚派、楊寶森的楊派、李少春的李派,他看到馬連良的藝術潛質、婉拒馬連良拜師之請、而玉成馬派與餘派、言派、高派的平起並立,他料定孟小冬是他最心儀繼承人,孟去港台傳餘,被許多傳人尊稱為孟派,孟始終堅稱「我只是餘派。」天意弄巧,一個世紀後,就在世稱「冬皇」的孟小冬幼時發跡的上海,又出現了一個世所公認的小孟小冬,從形象到聲韻,可謂酷肖,再現餘、孟風采,抑或餘、孟再世。觀眾有幸呼出:「天上掉下個王妹妹!」然而此餘派傳人,卻委實未見過餘,也未見過孟,卻盛名不虛,京劇史現此奇人,到底憑誰之功?叔巖教人、摳戲向來嚴謹,王珮瑜無緣親聆,如何變心儀為實受?珮瑜的出現實為京劇觀眾之大幸。而其未來之發展、走向又當如何?人言英雄不問出處,流派傳承或亦自順享天祺。公認為餘派優秀繼承人的她,未始不可蔚成她自己的王派或新餘派?不管她自己有無此想,時代使然,觀眾使然,京劇史使然,藝術規律使然。多少年,我們講繼承與發展,尤盼新流派脫穎而出,順時而生,難道,好龍的葉公會是我們自己嗎?
王珮瑜只想老老實實演戲,她把自己的生命全都融進了餘派。證明了「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即使無緣拜師,未經口傳心授,沒人一字一句摳,師爺的精髓也能學到手,當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王珮瑜有天分,但也要有機遇,要遇見貴人。上海京劇院支持她挖掘久違幾十年的譚鑫培、餘叔巖、譚富英都演過的骨子老戲《朱砂痣》,且找到秉持譚餘且尚可口傳譚餘唱腔的收藏家李錫祥先生,便是王珮瑜奉天承運的良機與貴師。
餘生也晚,看了一輩子京戲,今始得見早聞其名的《朱砂痣》。此確是一出令人拍案激賞的好戲。配得上譚、餘早年曾經的常演,也證明了王珮瑜的慧眼識珠和執意傳承。該劇既有餘派極佳而妙造的藝術風格,含英咀華,意蘊深湛,又伴有明顯的人物及立意的缺憾,有傷於餘派的完美與大雅,至譚、餘二先師未嘗多演至大成又旋而擱置,而身在新世紀的新生翹楚王珮瑜拿來上演,又是她未曾見過、也非觀眾渴望她重推的戲,何也?難道,她未經過或未聽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戲改與禁戲嗎?這戲經得起今人對傳統戲中某些封建意識的挑剔與批判嗎?筆者認為,王珮瑜的想法是明確的,即《朱砂痣》利大於弊,瑕不掩瑜,優秀遺產的瑕疵不應掩蓋以致拖累其應被保護與開掘的光華,也不會混淆或低估今天觀眾的認知。哪一部產生於舊時代的古典名著不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或思想局限呢?如都求全責備,我們的歷史文化則會是一片空白。我想,珮瑜對傳統和祖國文化遺產的識見與態度,值得我們學習。尤需要膽識,即使在今天。識得其優秀,見得其光彩,更需要真知。
《朱砂痣》又名《天降麒麟》《行善得子》,台詞簡練、故事動人、勸人向善,彰顯了「積德行善」「知恩必報」等中華優秀傳統美德,此立意是該戲最值得弘揚之處。全劇以唱功見長,有大段細膩婉轉、抑揚有致、有別於其他劇目的二黃慢板、原板、搖板、散板、四平調等唱腔,光華四濺,不啻珠玉,是該劇最值得傳承的餘派寶藏。2013年,王珮瑜向年屆耄耋的收藏家李錫祥先生學了該劇的唱腔,結合譚派和餘派的藝術風格,又根據自己多年學餘的體會和個人聲音的特點,精致打磨了該劇並重新排演,填補了該劇多年未演的空缺,再現且升華了餘派表演的藝術品貌。」像音像」的錄制與播出,將這出傳統骨子老戲得以再現,將餘派的從容優雅與恢宏精巧訴於當代,詮釋了餘派無與倫比的功力及可予今人欣賞的價值,給觀眾以極大的藝術享受,增強了餘派在人們心目中無可替代的想像及可與今天時尚對接的魅力。加上王珮瑜自身的異秉與風範,可以說,該劇的重生,實是餘派繼承與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葩。
《朱砂痣》教人向善的積極內涵,是該劇也是王珮瑜贏得口碑的一大原因。餘叔巖感嘆自己一生未創幾出新戲,雖未稍減其創立新譚派的光輝,卻也造成他未能攀向更高藝術巔峰和更遠大人生目標的憾事。王珮瑜替師爺也為自己彌補了這一憾事。雖然這不是一出屬於她的原創劇目或現代新戲,卻是一出經她發掘打造、別有光彩、獨具特色、發人深思的優秀傳統戲。向善是今人仍需認真遵循的做人之本,符合今天值得弘揚的道德價值觀,尤其作為該劇主人公,將正己與助人做成因果,將追求自己生命的完好及追求自我完美的內心角鬥置於戲劇矛盾的突出位置,不僅綻出餘派藝術的獨特、簡約、優雅、時尚,更具直抵觀眾內心的力量,從而顯示出一種難能可貴的生命密笈與現代風神。這一切,都體現在對人物性格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描繪中,體現在演員精彩而得體的演唱中。太守韓廷鳳與發妻、親子在兵亂中遇難,妻亡子失,他辭官隱居鄉里,因無子嗣,另娶江氏。新婚日見新娘啼泣,問起情由,知江氏因夫君吳惠泉病重,家中貧困,不得已賣身救夫。韓廷鳳頓生惻隱之心,贈銀送其返家。惠泉得錢病愈,攜妻登門拜謝,得知韓員外求子心切,告知欲去四川買得一童送與員外。吳果然買回贈韓。該童聰穎知禮,韓廷鳳喜愛非常,言談間懷疑孩童身世,驗得左腳掌有一朱砂痣,認出該童就是十三年前失散的親子韓玉印。父子喜獲重逢。《朱砂痣》的藝術成就更是餘派寶藏,當認真學習、保護與傳承。
《朱砂痣》開演二十幾分鐘,王珮瑜扮演的韓廷鳳上場,一亮相便贏得陣陣喝彩,雖為退隱太守,仍形神健碩;年逾半百,仍神采奕奕。剛開始,佩瑜唱做未全部放開,有些內斂,卻畫出其即將迎娶一少婦為妻的歡悅與期切。隨後,越唱越亮,越唱越覺味厚,展現了餘派老生「雲遮月」獨具的藝術特色。接下來面對娶進的新娘唱二黃慢板,風格漸趨奇譎,情感細膩,每句皆有變化,抑中有揚,波瀾不驚,心中竊喜,又夾有不安,幾句話問出端倪,聲色不露,即做出退婚、贈銀抉擇,命家院將該女送回。唱慢板前先叫板:「丫環掌燈,待我一觀!」十分響亮,至唱第一句慢板「借燈光暗地里細觀姣娘」,韓員外的內心是滿懷期待的,溢出不無激動的獲得感。燈下觀「嬌娘」的聲色、表情,心安理得又有些忐忑,合乎他的身份,與其此時的心情也很貼切。唱第二句:「我看她與前妻一樣風光」時聲音放開,一種似曾相識的情懷將他的心門打開,感到娶對了人,心跳加速。第三句情緒陡轉,「只見她愁眉皺淚流臉上」,聽到新娘哭聲,他立即想到「莫不是嫌我老難配鸞凰?」得知「不是。」倏然唱「要穿衣錦繡衫任你掉樣,你有甚心中事細說端詳,這有何妨?」表現了他對新婦的關愛、體恤和急欲獲取娘子心的切切。及至江氏道出原委,才引出韓員外的意外與震驚。他按住自己的心,緊打慢唱搖板「聽她言伊現有婦隨夫唱,怎奈我兩下里拆散鴛鴦。再不要做惡事天在頭上,自情願伴孤燈永守空房。」節奏與旋律的變化,及此前每一句演唱的輕重緩急,都讓觀眾感到韓員外內心的恍惚。這恍惚體現在演員每一字一腔的字韻、腔格、平突、緩急、歸音、氣口乃至內心的細波微瀾中,均有層次地送到觀眾的心里。
觀眾讚賞餘派,不僅在有味兒、好聽,實是感到其塑造人物的生動、細膩,立意表達得準確、鮮活。我們聽王珮瑜唱《打侄上墳》《桑園寄子》,也會有類似的感受。但同是員外戲,同是演樂於助人的慈心善舉,唱同樣的慢板或搖板、散板,每個戲不同,每段唱的每一句也不同,不會因京劇唱腔板式與調式的程式化規矩而大同小異甚或「一道湯」,有造詣的藝術家總會在同、異間做文章、找俏頭、覓新意、現異彩,於細微處刻畫人物,於無聲處弄潮揚波。這正是餘派的藝術特徵,也是流派藝術所以形成的秘密,亦可見京劇之博大精深。
韓員外的內心波瀾,使他沒有流於概念化、一般化或直奔主題的高台教化,凸現了餘派演唱重人物性格發展、重人物內心揭示、重情景描摹與情境營造的優長,正顯現了中國戲曲文化的俗中見雅和氣韻萬千。戲劇最主要和最集中的任務是揭示人的存在和成長,戲劇衝突最可貴的是表現人自身的矛盾衝突和人戰勝自己的內心力量。聆聽和感受餘派唱腔每一段、每一句、不同板式、不同調性傳遞給我們的細微、簡約的律動與回旋,對我們不僅是欣賞,是享受,是慰藉,甚至是療傷。經過由喜悅,到期盼、到質疑、到關切、到驚覺、到警醒、到毅然轉向和決然放棄,韓員外及時做出了向善之舉,清晰可信地表現了一個有良心有道德人的心理變化。這變化好在細微,予人咀嚼品味,又妙在瞬忽,令人不遑擊節。讓我們看到了人應該怎樣不忘做一個真正的人?如何一旦發現錯誤、即時更張、平心正己、洗滌污穢、清平世界?可見,做一個好人,難,也不難,關鍵在想不想做,以及舍不捨得付出代價。無疑,這樣的優秀劇目從內容到形式都值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繼承與弘揚。
接下來,韓員外靜場唱二黃原板,憶起「遇兵荒妻和子無有下梢」,嘎調連翻,全場報以雷鳴般喝彩聲。台下戲迷情不自禁跟著哼唱起來。戲後,不少老戲迷表示王佩瑜的嘎調可媲美帕瓦羅蒂,而年輕粉絲則聽出了餘派特有的「海豚音」。這激動的高腔道出了韓員外難忘的悲慘經歷和不泯心結,也雜糅了對自己沒有走錯路的慶幸。
王佩瑜在唱腔上淋漓盡致,在人物塑造上深入細致。她扮演的韓員外,退役太守,依然直挺,情緒飽滿,動作沉穩,思維有序。後面,看到送來當兒子的孩童時,先不知這是自己的親生兒子,但已父愛爆棚,王佩瑜通過幾聲充滿溺愛的笑表現出老來得子的歡悅,台下觀眾也為之竊喜,溢出「善有善報」的喜劇風格。不僅如此,當吳慧泉攜妻去韓員外家謝恩時,二人邊走邊唱,一人一句搖板唱到進入吳家、跪在韓員外面前。吳唱:「我和你到他家雙膝跪倒。」江唱:「我夫妻特地來叩謝恩勞。」這樣連唱帶做甚至連時空轉換於一爐已屬創新,韓員外突見他夫妻二人跪在自己腳下時,驚愕得不知所以,竟唱出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實難想像、又極為奇特的幹起碰板四平調。
韓廷鳳慌亂地不知先面對誰攙扶誰,只聽他「哎呀」一聲,對吳唱:「我救人的急,救人的難,救你的貧困。」又忙不迭對江氏唱:「我全爾的節,全爾的義,全爾的婚姻。」此時,傳統四平調的板式與旋律全部被打破,變為只能由此時此地韓員外驚悸不已隨心唱出的誰都不知道的節律與怪腔。觀眾只剩下驚嘆與嘖嘖,直呼:「太過癮了!」
餘叔巖對譚鑫培老師傳授給他的戲,不僅吃深吃透,精磨細研,而且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變革,蔚出新意,創出餘派。他對傳統的繼承與發展,適可成為後世的先師與楷模。流傳至今的無生不餘,不僅證明了餘叔巖的藝術常青,更留下了任何藝術都需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生長。王珮瑜的藝術道路還很長。餘、孟先師的安享不在看到舊時他們的模樣,而在聽到嶄新生命勇於沖出母腹的吶喊。讀懂先師的優長和發現先師的不足,是有志於繼承前輩走向未來必須擁有的兩翼,是任何事物不能避免的新陳代謝。我們應做勇於推陳出新的革新者。
《朱砂痣》源自傳統,雜有缺憾不足為奇。缺憾不在舍妻得子,善有善報,叨宿命論之嫌,而在人物塑造的不統一,不完美,有悖於今人的審美期許。這也是不應苛求於古人的。但可以和應該以今天的眼光審視之。韓員外既憐恤吳慧泉因貧困忍痛賣妻,毅然贈銀還妻,何不憐恤四川老嫗因貧困賣子的無奈與痛苦?緣何同意他人遠去買童贈己以向自己報恩?不忍買人妻,而忍買人子,豈不矛盾?這前後的韓員外還是同一個人嗎?此舉或反使韓員外的善有善報有可能淪為他自己有意構築的陷阱。
說到「善惡到頭終須報」,其實是千百年來中國老百姓矚望社會也警示自己的一種良好願望,期冀人心大於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及正義必勝的吶喊。《清風亭》天雷劈死張繼寶,始終深得人心,不僅符合廣大人民的願望,也是對大陸傳統孝道的尊重與維護。不會有人質疑其為「宿命論」。感恩與報恩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人之成其為人的根本。君不見,一度被禁演的程派名劇《鎖麟囊》終又重新走回人民大眾,予人以「施恩不圖報」和「知恩必報」同樣的陽光雨露,將「宿命論」棄之不理。同意買孩子送自己則不同,於法於理都難為今天觀眾認同。時代進步了,觀眾視野中的韓員外應展現出更美好和理想的人格與人性。
對傳統戲的整理改編是改戲乃至改制、改人與生俱來的好辦法。今天仍活躍在舞台上的許多好戲,都得益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整理改編,從而煥然一新,成為新中國「三並舉」中不可或缺和促進新編劇目成長與進步的源頭與力量。
筆者以為,《朱砂痣》改編不難,可以改動一些情節:吳慧泉買孩子,韓員外事先不知,贈孩時先是不受,見錯已鑄成,問明原委,至看到孩子腳上朱砂痣,確認是自己親兒,喜不自禁,反而提出要去接回貧困的賣子老婦,使其晚景無虞,且教子懂得養母之恩。吳慧泉也感悟良多,只恨自己未能報恩。韓員外說:「麻煩你幫我再找到那賣子之人,去掉我心病,就是對我最大的報答了。」
對於餘派的傳承、發展,王珮瑜身負重任。未來,我們希望聽到餘、孟、王的一脈叮當響得愈來愈明麗、優雅、綿長、久遠。
長按二維碼關注中國藝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