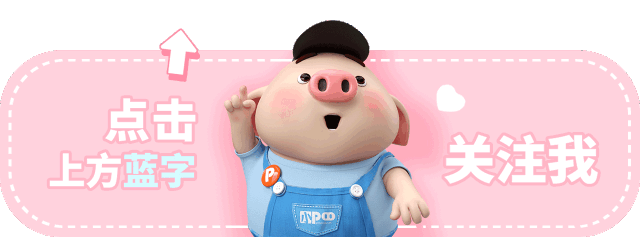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帝國的暮光:
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
[美] 魯大維著
李梅花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11月出版
444頁,72.00元
━━━━
文︱馮立君
「蒙古帝國史是世界史,反之亦然。」梅天穆(Timothy May)如是總結。他回顧了約翰·安德魯·波伊勒(John Andrew Boyle)的「蒙古世界帝國」理念、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對蒙古史研究中亞史料的強調、林蔚(Arthur Waldron)論及的蒙古是現代史開端的觀點、大衛·摩根(David Morgan)對蒙古之於歐洲重要性的論證、托馬斯·愛爾森(Thomas Allsen)從歐亞整體對於蒙古帝國的廣泛研討、莫里斯·羅沙比(Morris Rossabi)關於忽必烈和景教的研究,並做出這一論斷(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Reaktion Books, 2012。中譯本《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馬曉林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導言)。這一見解雖並不能說已是學界共識,但至少反對的人越來越少。然而,他多少有些忽視作為蒙古帝國歐亞一體之一環的東北亞區域,以及對此區域著力最深的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學者的研究。這一區域雖然與大都近在咫尺,但或許是因其政治體規模和數量並不可觀,似乎在梅氏的學術史回顧中成了「邊緣地帶」。事實果真如此嗎?
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謙遜地將杉山正明和愛爾森視為基於全球視野考察蒙古帝國歷史的代表人物,而宣稱自己的作品《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中譯本甲骨文叢書,2019,李梅花譯,以下簡稱《帝國》)相對縮小了研究範圍,只是針對帝國東北部的研究。他的研究與之前的學者相比有很大不同。《帝國》針對蒙古時代後期歷史研究中對「共時多維」和「歷時變遷」把握的缺失,將蒙古帝國作為一個整體闡釋,但將焦點聚集在東北亞地區,強調在歐亞一體視域中對蒙古治之下東北亞區域的動態研究。他充分參考了西文撰著的蒙古史著作,更大量吸收中文、日文、韓文研究成果。需要指出,作者對於東北亞的定義也與以往學界大異其趣:他在地理上強調遼東南部、高麗境內、大都周圍及山東一帶及其聯繫,換言之,可以稱為以政治關係為中心視角而並非局限於地理意涵的歐亞大陸東北部。這與宋念申最近以近代東北為主要觀察窗口,結合了中國東北及其周邊區域在古代歷史上的政治地位的獨特性提出的「東北歐亞」概念頗有神似之處,而宋氏是「將這個邊緣地帶看作歐亞大陸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區域,並探討其獨立於周邊國家的內在歷史動力」(《作為歷史中心的東北歐亞:理解東北興衰的一種視角》,《開放時代》2019年第六期)。他們站位於不同時代,選取的中心視角則異曲同工,而且宋氏同樣認為蒙古時代是東北歐亞族群發展的一個分水嶺。
蒙古帝國東北部最重要的政治體是高麗國。魯大維這部《帝國》,既是蒙古帝國史的局部區域(高麗及其他地方勢力)研究,也是從高麗史擴大到蒙古時代東北歐亞政治關係的嘗試。在這種互動互換的交錯視角中,《帝國》的展開至少有如下三大看點。當然,他的學術貢獻和學術趣味絕不止於此。
元大都的高麗王
忽必烈之所以選擇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帶作為大蒙古帝國的新都城,杉山正明的解釋(《忽必烈的挑戰》,周俊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可以理解為,大都的選址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它既鄰近出海口又兼顧中原農耕地帶和草原遊牧地帶,是兼跨歐亞多種經濟區域的龐大帝國的理想政治中心。妹尾達彥關於古都長安的研究(《長安的都市規劃》,高兵兵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也啟示著人們,與北京同樣處於東部歐亞的半月形農牧交叉帶上的西安,因其居於陸上絲綢之路聯結西域、運河水運聯結中國東部的交通樞紐,同樣便於控馭東部歐亞農耕與遊牧南北兩大經濟區(參閱李鴻賓《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二期),加上關中易守難攻的軍事優勢、沃野千里的農業相對優勢,西安和北京得以分別成為中華帝國前期(秦漢隋唐)和後期(元明清)的兩大主要都城,各領風騷一千年。而中華帝國前期主要以長安為都(輔以長安—洛陽交替),後期以北京為主(輔以南京等地替代),又與北方族群的崛興遞嬗自西徂東轉移有著內在的歷史聯動。
元帝國的汗八里是一座五光十色的繁華都市。這是一個蒙古人真正開啟了世界史的時代(杉山正明《蒙古顛覆世界史》,周俊宇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歐亞陸海世界的聯通和暢行是空前的,官旅商人從東亞去往中亞、歐洲並非難事,歐陸北非的人群旅居中國更絕非稀罕。前者有拉班·掃馬(Rabban Sauma)、長春真人丘處機等,後者則有馬可·波羅(Marco Polo)、伊本·巴圖塔(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等等,他們都留下了供後人閱覽的紀行文本。在傳統中華帝國的朝貢圈域範圍內,這一時代在帝國京城的見聞與前代相比顯得迥然不同。最典型的莫過於從朝鮮半島的高麗王國的來訪者。以往在隋唐帝國時代,新羅國王派往中國的使臣首先要克服海上漂泊的艱險,繼而是在中國東部沿海登陸之後的陸上長途跋涉,他們在長安的鴻臚館得到上國朝廷的熱情接待,向皇帝獻上本國方物和貢品,有時還包括美人,並代國王領受天子給予的官爵冊封。新羅王朝貢中華至誠,玄宗皇帝在安史之亂中罹難奔逃西蜀,新羅的使臣竟然追到成都獻禮。即便如此,在漢字文化圈的禮治體系中,朝貢國在位君主一般不會親自前往宗主國都城朝覲(參閱馮立君《唐朝與東亞》,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然而,在大元帝國和高麗王朝的時代,這一切都變了樣。不僅在大都城中,幾代國王長期滯留不歸,而且他們的身份也十分多元複雜。這一切變化根本上是如何發生的?
高麗(918-1392)是繼新羅之後再度統一了朝鮮半島的王朝國家,其政治體模式最初仍然是基於對中華帝國巨型政治體模式的摹仿和本土傳統的融合。五代亂世,高麗興起於新羅北方,通過逐步消滅國內割據勢力,完成國土的政治一元化,在以國王為頂端的官僚貴族聯合政權體制中,以農業為主的高麗國家繼續輸入和消化來自大陸的漢字、典章、佛教、儒學等文明成果;同時,伴隨著中原王朝相對於北族王朝在軍事上衰落和劣勢,高麗民族意識抬頭,其君主甚至一度稱帝,並且不斷向北方開疆拓土,這一所謂「北進」並未因契丹遼帝國的多次入侵而遭到實質上的停頓,相反陰差陽錯地將邊界推進到鴨綠江附近。蒙古人在草原崛起,以氣吞山河之勢橫掃歐亞,大元帝國統一西夏、南宋、金國等地,針對東方的高麗政策也進入全新的時代。
譬如,高麗國王的廟號都要改正,以往非「祖」即「宗」的廟謚,一變而為以忠字開頭的「忠×王」模式,這「忠」當然是忠於大元兀魯思:高麗王既是本國君主,又是帝國臣僚。隋唐時代新羅王往往襲封樂浪郡王或是寧海軍使、雞林州都督一類官爵,以示藩屬之意。正如大唐帝國對於蔥嶺以西諸國的羈縻州府設置,更多的是徒具形式,僅僅表示一種隸屬關係(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335頁)一樣,唐朝對東亞諸國與此類似,並不直接干預其內部政務。然而,蒙古帝國治下的高麗,自元宗、英宗以後,高麗君主相繼以忠烈王、忠宣王、忠肅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的名分載入史冊,帝國對於其內部干預和控制已然空前強化。
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就是,從忠烈王到恭愍王的幾代高麗國王,不僅不同程度地蒙古化了,而且因為各種因緣往往長期在大都逗留。我們可以忠宣王為中心來通覽:忠宣王,蒙古名益智禮普化(意為小公牛),母親為元世祖忽必烈之女,自己也娶元朝皇室女為妻。這位奇特國王剛即位不久即遭廢黜,隨後滯留大都十年,後來復位也沒有回國久居,仍返回中國生活。因為卷入帝國宮廷政治,在元英宗登基後被流放吐蕃,其後得以北返,最終薨逝於大都。他的父親忠烈王也曾在華居停一年半。他的次子忠肅王,蒙古名阿剌訥忒失里,先後迎娶三位元朝公主,被扣押在大都四年之久,其時高麗險遭廢國立省危機。忠宣王的孫子忠惠王也很傳奇,最初以世子身份入元為質,因與元朝貴族燕帖木兒過從甚密得以第一次即位,又由勾結流放高麗的元朝皇子妥懽帖睦爾的嫌疑而第一次被廢;忠肅王死後,元朝丞相伯顏不同意他繼位,忠惠王被帶至元朝受審,後雖得以復位,但是開罪元順帝奇皇后家族,第二次被廢並押送元朝,最終在流放廣東揭陽的途中死去。身在大都的高麗君王(或儲君)身份複雜,他們與皇室有姻親關係,不斷卷入蒙古宮廷政爭,從而影響高麗政局。這本質上是由於大元帝國對高麗王國的控制和兩國的獨特關係形態造成的,元朝規定:高麗國王要娶蒙古公主為後,且儲君要在大都蒙古宮廷受教育。
忠宣王的另一個孫子,恭愍王——魯大維稱《帝國》這本書是「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其中一個男人就是這位高麗國王——王顓,蒙古名為伯顏帖木兒,他登基為王以前也在元大都入質十年。但是他的政治作為與他的祖父和父輩相當不同。大蒙古兀魯思促使他走上高麗至高無上的權力巔峰,同樣也帶給他一系列的挑戰:在宗主國的強勢主導下,他依托高麗出身的元朝皇后奇氏的勢力攫取王位;親政之後從親元走向反元,大刀闊斧改革高麗弊政之際;蒙古大軍壓境,他又從一個強力君王變成捨棄京城不斷南逃的虛弱國王;光復開京回師,他又面臨如何措置權臣的難題……《帝國》基於多元動態(而非二元或靜態)的政治關係而展開全書,從高麗史的角度,幾乎可以視作一部「恭愍王應戰史」。無論是蒙麗關係史,抑或高麗史的研究,這都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切入方式。
流放高麗的蒙古王子
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歷史學家的技藝》曾說:「歷史學所要掌握的正是人類」,舉凡「地形特徵、工具和機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獻、似乎是與其締造者完全脫離的制度,而在所有這些東西背後的是人類。」(張和聲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23頁)按照我們的理解,地理、制度、器物、文本並非歷史學的終極旨歸,歷史研究的核心仍然是活生生的人:碎片終究要拼出全圖來。在《帝國》這部風格獨特的作品中,蒙古帝國與高麗及其周邊勢力的多元互動關係的揭櫫,實際上是通過刻畫妥懽帖睦爾、奇皇后、恭愍王及其周圍的一乾人物的群像得以完成的。
恭愍王是高麗後期史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這里姑且不談。奇皇后則確實稱奇,她經元朝與高麗之間的貢女制度而進入帝都宮掖,借由自身的伶俐和美貌逐漸攀升至第二皇后,被賜蒙古姓肅良合,蒙古名完者忽都,終於成為帝國皇后,她誕下的皇子愛猷識理答臘最終成了惠宗的繼承者,只是大元帝國其時業已迫最近暮,江山斷送殆盡。後世有說法認為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外國」意義上的皇后,實際上從蒙古帝國歐亞一體世界的角度而言,特別是蒙麗上層跨越數代非同一般的互相通婚事實來看,高麗出身的皇后在當時並不被當做什麼外國人,這種定位只是當代民族國家情結的一種反映罷了。《帝國》一書在圍繞高麗與大元兀魯思關係的專章里為她做過特寫,同時將其作為恭愍王上台及其改革的最重要的背景勢力,奇皇后可以理解為構成大元帝國多彩畫卷中的高麗色彩,一個別致的象徵符號。遍數歷代王朝,唯此一枝獨秀。高麗—元朝時代特殊性也由此彰顯出來。
她的夫君元惠宗,明朝上尊號為「元順帝」,又一位在位時間頗長,而且是前期勵精圖治、後期朝政懈怠的帝王,或可與漢武帝、唐玄宗這些頗具爭議的皇帝比肩。但是他的登基之路則遠更為艱難曲折。父汗被弒,作為儲君,他先是遭流放高麗大青島,幾度春秋,大都政局波譎雲詭,他又轉而流放廣西靜江(今桂林)。歷史在這里意味深長地點了一個逗號。高麗全境曾不止一次被改為征東行省,國王兼任行省長官,而且鄰近大陸的濟州島更是因其歷史上與朝鮮半島若即若離的政治隸屬關係和元軍在這里剿滅反元的「三別抄」而曾直接歸入大元版圖,稱「耽羅軍民總管府」,成為元朝牧馬地之一。現政權的威脅者妥懽帖睦爾流放高麗大青島,再度證明包括海島在內的高麗全境與元朝內政之間密切的聯繫。
魯大維的筆觸是以惠宗皇帝在位期間與恭愍王的互動作為對象,這幅關於遲暮帝國的宏闊畫卷對於與高麗相關的人事有著細致到驚人的描摹。同時,惠宗是這一時代的最高執權者,作者目為攪動歐亞東部的紅巾軍戰爭實際上也與這位大汗兼皇帝的政令和作為息息相關。圍繞著大都的元惠宗和奇皇后、開京的恭愍王、中原大地如火如荼的紅巾軍以及包括東北亞在內的帝國各地將領和官員對於鎮壓紅巾軍的機會主義和利己主義行為方式,《帝國》的描寫並不刻意:人物在利益關係面前不受控制,自我完成其使命,歷史的劇情發展不為史家干預,史家是在劇目選定中寄托了無言的見解。《帝國》自我設定的四大主題——區域視角對王朝研究的必要性,蒙古治下的大融合及其影響,個人和家族利益凌駕王朝之上,高麗是大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從大青島流放就已奠定,但是作者仍然在一般史識之外抉取紅巾軍這一富於時代特徵的個案,借以剖開歷史橫斷面。作為讀者,我的感覺是惠宗的刻畫並不集中,也不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深思起來,所有的枝蔓關係又都收攏於他:從至元到至正,罷黜伯顏,任用脫脫,朝綱扭轉之間,帝國內部融合與反崩裂的根本動力難道不都是來自這位皇帝嗎?
這樣看來,這部著作通過精心的史料剪裁,奉獻給讀者的似乎是蘭克式的以人物和事件為中心的歷史敘事: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鮮明突出,細節呈現引人入勝。這些就是這部作品的全部嗎?
魯大維的挑戰
韓國學者金翰奎2004年出版了一部區域通史《遼東史》(김한규『요동사』,문학과지성사,2004),提出一種「第三歷史共同體」的觀點。從他這部與其他諸多的彌漫著民族主義情緒的東北亞古代史研究極為不同的著作中,我們不難得出,在中原王朝和朝鮮半島政權之間,中國東北地區(即遼東)族群和政權的演進史表明,該地區存在著與現代民族國家視域下「非中即韓」思維定式迥異其趣的一種「自在的」歷史邏輯。從金翰奎到宋念申,一種新的歷史敘事不同於中原中心—東北邊緣二元互動模式並對後者提出挑戰。這一富於啟迪和解放意味的學術思考成果,理應獲得更多的討論,遺憾的是事與願違。
與金翰奎試圖貫通整個古代史作為例證,以及宋念申立足當下多元邊疆的回望都有所不同,魯大維的《帝國》的意義是基於一個斷代(蒙古帝國時代後期),重新構建出一個研究單元(東北亞)。無論是稱之為東北亞也好,東北歐亞也好,朝鮮半島與遼東、山東、華北的互動在歷史上很少缺席,朝鮮半島更從來不是一個自外於大陸的封閉單元。這並非一個簡單的觀看角度問題,在實證的分析中需要費力挖掘史料具體論證。例如,在當時介於大都和高麗之間的遼東地區(遼陽行省),當地的官員和人事、機構中,高麗人竟然有諸多參與,作者不厭其詳地舉證韓永、崔瀣、安軸、趙廉、李轂等一眾高麗士人通過科舉等途徑出仕遼東,大大補苴了諸多強調蒙古帝國泛歐亞發展局面的學者們鮮少涉及的東部地區種族融合細貌。不惟是研究視角,本身即歷史研究路徑。
中國學者關於十至十四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也十分強調從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出發,北向東北亞延伸至高麗,並沿半島西海岸南下,經日本九州和西南諸島、琉球群島一帶的東北亞航線和中國東南沿海向西南延伸,經中南半島南下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抵達紅海乃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線形成的網路作用(魏志江、魏楚雄《論十至十四世紀中韓海上絲綢之路與東亞海域交涉網路的形成》,《江海學刊》2015年第三期)。與之對照,魯大維的蒙古帝國東北亞區域研究具有一種超地理的特性,其間的政治關係(也就是非只限於地理因素的人事)成為歷史單元構建的核心要素。
當然,這並非是作者的主觀刻意建構,在《廣角鏡》這一章,作者著力論述的14世紀東亞外交網路,重新思考元帝國及其各地方勢力與高麗共同面對的紅巾軍戰爭影響,揭示出元帝國地方勢力的強力崛起,恭愍王除了向大都的元朝皇帝和皇太子、貴族貢禮,也向南方的張士誠、朱元璋,遼東的東方三王家代表人物納哈出,女真人的首領,日本的足利幕府和九州地方官分別贈送禮物,作者將這種「超流動性」看作大元帝國衰落、地方擴張勢力的標誌。在紅巾軍最終直接或間接造成大元與高麗的雙雙崩毀前,兩國的邊界處於相互滲透的狀態。這些歷史真實並不會以歷史學家的視角而轉移,也就是說,正是作者的超越性視角清晰有效而準確地捕捉到這些歷史真相,使蒙古時代史的研究向前推進了。
1368年,暮靄籠罩整個帝國,妥懽帖睦爾率眾北出健德門,永遠離開了大都。全書並沒有在此戛然而止,作者又將目光投向大明、北元、高麗並峙的時代。恭愍王面臨著新的抉擇和挑戰,當然,轉換視角,那也是草原中國和南方中國的面臨的挑戰:東部歐亞政治版圖的更迭並未畫上休止符。多年以後,高麗王的親北元繼任者向遼東派出一支大軍進攻明軍,然而這股由李成桂指揮的勁旅在鴨綠江附近回師京城,高麗五百年王統這一次沒有經受住挑戰。隨後,當來到南京的使臣向大明皇廷求取新王朝的國號時,太祖皇帝一錘定音:「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從健德門的暮光到應天府的曙光,東北亞政局從來不曾離開中華帝國的視野。海東君王的挑戰,從來也都不只是他自己的難題。
話說回來,在蒙古帝國歐亞作為整體的前提下,聚焦超政治體的區域聯動一體的研究范式,是不是可以看做魯大維先生對現有蒙古史研究的挑戰呢?同時,它對於其他斷代比如唐史、明史或清史研究是不是也具有啟發意義呢?這種見仁見智的問題,相信列位讀者親自讀過這部作品之後會有明確的答案。
掩卷之際,不意讀到魯大維新作《明代中國及其盟友:帝國統治歐亞》(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出版預告。一位學者的創造力的一個最重要表現無疑就是他源源不斷的學術作品,如果說他已經出版的《明朝尚武奇觀》(Martial Spectacles of the Ming Cour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聚焦的是明帝國對於狩獵、騎射、馬球等戎事活動的濃厚興趣從而凸顯其非同一般的王朝特性,那麼這部新著則將致力於探討明帝國如何看待和措置內亞鄰邦包括蒙古諸部關係的全 新髮現。而我們知道,他對於高麗末、朝鮮初的著名政治家鄭道傳,也有一部專著問世(Seeking order in a tumultuous age : the writings of Chong Tojon, a Korean neo-Confucia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顯然,魯大維的學術疆域不僅幅員遼闊,而且蓄力向縱深挺進。
我不禁在想,這也是優秀學者對自己發起的挑戰。
馮立君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ND·
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歡迎點擊下載「澎湃新聞」app訂閱。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訪問《上海書評》主頁(shrb.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