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原創: 宋烈毅 文學報

(刊發於文學報2013年6月6日)
把裝在籃子里的貓丟掉卻又不得不將它們從河邊帶回來,這樣的事發生在薩特的長篇小說——《自由的道路》三部曲的第一部《理智之年》中。
在小說的第七章,薩特設計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情節讓這個叫達尼爾的男人和讀者「見面」,即,他以一種慣有的慢條斯理的敘述風格講述了達尼爾將他飼養的三只貓帶到塞納河邊並試圖將它們淹死的經過。一路上,達尼爾提著那只沉甸甸的裝著三只貓的籃子的感覺是非常奇特和詭異的:
達尼爾加快步子,鑽進了一條通向塞納河的骯髒的小街。街道兩邊,擺滿了大酒桶的客棧。這時,籃子里不停地‘嗷嗷’叫起來,而達尼爾幾乎是在跑了——他提的是一只漏了水的桶,水正在一滴滴地流掉,每一聲貓叫,都是一滴水。
——將一只裝著三只可憐的貓的籃子比喻成一只漏水的桶有著一種驚人的直覺在里面,通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貓的哀鳴和水滴的感覺互通。從常理來講,貓的叫聲總是一聲聲的,有間隔的,這和水滴的性質是相似的。在貓的叫聲就像水滴那樣從柳條籃里一滴滴地流掉的感覺中,達尼爾陷入一種虛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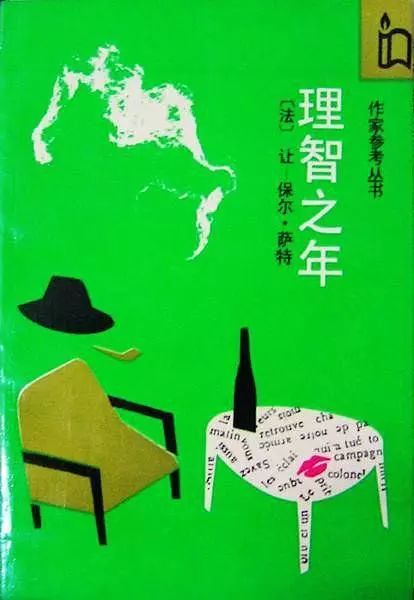
展開全文
《理智之年》在薩特創作中占有突出地位。它表明了「二戰」之後薩特對自由的嶄新理解,形象地表現了「他人就是地獄」的存在主義觀點,與西方敘事文學傳統及其現代發展構成了互文關係。
實際上,從達尼爾一開始把這些貓塞進柳條籃里,他就陷入了虛空,他要處理和對付的事物呈現出不可捉摸的詭異面孔,在「貓」與「非貓」的感覺中來回擺動。
在這些貓被關進帶有蓋子和兩個扣鎖的柳條籃里之前,它們是以「非貓」的身份出現的,所謂「非貓」,從小說的描寫看來其實就是人和貓相處的一種關係錯亂。不錯,在小說中達尼爾就是將這些貓當作人來相處的,我們先來看看達尼爾是如何挑逗他的母貓「瑪爾維納」的吧:
……達尼爾不像喜歡另外兩只貓那樣喜歡它,因為它總是虛情假意,而且一副奴性。當它發現主人在看它,便從老遠就開始‘呼呼’響了,做成一副媚態:用頭在門上蹭來蹭去。達尼爾用手指摸了一下它肥大的脖子,它馬上就四腳朝天地仰在地上,達尼爾就搔著它黑色皮毛里的小乳頭。‘喵!嗚!——喵嗚!’他嘴里唱也似地哼著。那貓更得意地做著媚態,不停地翻滾著身子。
很顯然,母貓瑪爾維納是以一種女性的角色出現在達尼爾的生活中的,給他的焦躁而沉悶的生活帶來了樂趣,盡管達尼爾「不像喜歡另外兩只貓那樣喜歡它」。那麼另外的兩只貓呢?它們是否真的就被達尼爾所寵愛呢?非也。從小野貓「包比」的身上,達尼爾找到的是受虐狂般的快感,但這快感中也夾雜著焦慮。而對於第三只貓「西皮翁」,達尼爾似乎較為冷淡,這似乎和「西皮翁」的脾氣較為溫和有關,就像某個家庭中性格溫和、十分聽話卻並不出色的某個成員:
達尼爾的手表指著十點二十五分。他推開廚房的門,吹了一聲口哨。西皮翁第一個出現,它白褐色,生著幾根小鬍鬚。它使勁盯著達尼爾,野性地打了個哈欠,把腰弓了起來,達尼爾輕輕蹲下來,開始撫摸它的鼻子。那貓微閉著眼睛,用爪子一下下輕搔著他的袖子。
——就像一個並非虛擬的家庭,達尼爾和他的貓們都找到了各自的家庭角色。
而貓畢竟是貓,在達尼爾不留神將自己的臉刮破的一個燥熱的上午,他突然產生了要將這些貓處理掉的念頭:「他看到大柳竹籃子,在房間正中打開著蓋子。他轉過眼去:這是今天要用的。」
這是一個讓達尼爾重新找回房間里的主人翁意識的上午,對於自己房間的重新打量使得達尼爾做出了這樣一個突然的決定。人的優越感或許正在於小說中達尼爾所認為的「他喜歡他的房間,因為它非誰莫屬,也不會把他丟開」,的確,作為生活的一種鏡像,在小說中我們似乎也從未看見過與「把貓裝進籃子里丟掉」相反的情形,換句話說就是:人不可能被他養的貓裝進籃子里扔掉。

薩特是著名的愛貓之人,寫作時也要抱著寵物貓「虛無」
所以,在小說接下來所敘述的達尼爾拎著沉重的籃子試圖溺貓的文字中,我們嗅到的是人的驕橫自大和欲望種種。在將這些貓塞進籃子里之後,達尼爾開始了他的詛咒和謾罵:「怎麼這麼重,這該死的畜生!」被關進柳條籃里的貓們重又恢復它們的本來身份:「他只要把這三個畜生關在一個柳條籃子里,於是它們就又變成了貓,簡簡單單的貓,小小的富於虛榮心的哺乳動物,眼光短淺而正害怕得要死的小動物——最低賤不過了。」
與一群貓同處一室,最終對達尼爾的生活構成了某種挑戰。而貓的不可掌控不僅僅是因為貓同家中其他的寵物一樣是一個活物,更由於房間的主人與貓的關係出現了錯亂。因此,達尼爾把這些無法控制的貓關進籠子似的柳條籃里是為了找回「做人」的感覺,但這種感覺,照我們看來似乎有些過火。這「過火」的努力去「做人」的感覺是極其荒謬的,當達尼爾把他的寵物們統統塞進籃子里後,「在樓道里,他感到自己年輕而果敢,體內一股味,一股生肉之味」。我們應該意識到的是,在貓們被禁閉之後,一種悄然發生的變化是:貓的主人發生了變形記,他暴露出來的殘忍內心使得他更像一只野貓。在薩特小說《理智之年》的這個描寫「丟貓」的漫長章節中,貓的影子在不停幻變,撲朔迷離。
而關在籃子里的貓也不總是安分的,它們一路上發出「嗷嗷」的叫聲,那叫聲就像「水滴」慢慢地流掉,在感覺貓的叫聲像水滴一樣流掉的感覺中,達尼爾肯定有一種擔心。這種奇詭的感覺令「丟貓」的人一路上神情恍惚,試想一下,當一只桶里的水漏光的時候,桶也就空了,而貓的叫聲如果全部地「漏」掉,那麼貓們應該是奄奄一息的了。
所以,達尼爾也並非完全希望這些被他塞進籃子里的貓死掉的,包括他後來神情恍惚地拎著籃子來到塞納河邊,在一種懺悔的心情中寬恕了他的貓們和他自己。把貓塞進籃子里試圖拴上繩子綁住石塊沉到河水里而最終無功而返,在這樣的故事里,小說作者需要的是一種共振,同小說所講述的大故事的共振。
《理智之年》講述的是哲學教員馬跌為了女友瑪爾賽拉墮胎四處奔走借錢,因為馬跌的朋友經紀人達尼爾利用此事向馬跌公開了他與瑪爾賽拉私通的事,馬跌被迫偷錢給女友墮胎,結果是瑪爾賽拉憤怒地趕走了馬跌,達尼爾順理成章地與瑪爾賽拉結婚。「墮胎」同「丟貓」有著一種相似,正如達尼爾在將自己臉上的一個膿皰刮破的悶熱上午產生了要將家里的貓丟掉的想法那樣,馬跌一個人在夏日的大街上行走時突然意識到夏天來了,而「瑪爾賽拉懷孕了,這個夏天不同尋常」。尚未誕生的「胎兒」被瑪爾賽拉視作「像她一樣不幸的東西,一個荒誕的多餘的生命」,而在房間里肆無忌憚的貓們被達尼爾看作自己生活的挑釁者,乃至認為它們是多餘的,已無在房間里和他共處的必要。
就像一個連環套,《理智之年》在圍繞著馬跌替女友「墮胎」借錢的大故事里套著達尼爾「丟貓」的小故事,兩個故事相輔相成,都有著非常荒謬的意味。

1955年,薩特和女友波伏娃訪問中國。10月1日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新中國成立6周年的慶典。
與薩特的長篇小說《理智之年》中這個冗長的描寫「丟貓」的故事情節不同,我在魯迅的「手記小說」《傷逝》中所讀到「扔狗」的片段含蓄而簡潔,而且「扔狗」的動機清晰明了,全然是因為「我們」「早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來」。根本不像薩特的「丟貓」那樣費盡口舌:「倘使插了草標到廟市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罷,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願這樣做。終於是用包袱蒙著頭,由我帶到西郊去放掉了,還要追上來,便推在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里。」——或許狗的馴良是貓所無法比擬的吧,只需「用包袱蒙著頭」就可以了,而且也只是扔掉,「推在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里」。
在小說里,我們看到的凡此種種將家中的寵物扔掉的故事,大多有著相似的對於動物們「有益」的結局,就像達尼爾垂頭喪氣地帶著他的貓們返回家中,被涓生扔棄的叭兒狗「阿隨」也最終在「一個陰沉的上午」突然找回了家中,盡管它已是「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試圖溺死的、丟棄的這些寵物,在小說的主人公們經歷一番痛苦的心理歷程後,重新被小說家們安排「回來」,其間讓作為讀者的我們感受了情節的波折和心理的跌宕,這對於大家都是有益的。而「回來」更像是一種貼心的安慰,抒情淒美的《傷逝》需要,荒謬無緒的《理智之年》更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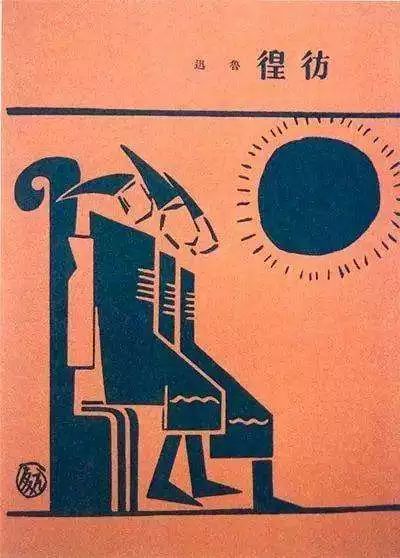
《傷逝》作於1925年10月21日,1926年9月收入小說集《彷徨》(上左)。此後被改編為多種藝術形式,如電影(左下)及歌劇(右下)。


新媒體編輯:李凌俊

文學照亮生活
網站:wxb.whb.cn
郵發代號:3-22
原標題:《為何在薩特和魯迅書中,被遺棄的動物最終命運反轉?| 此刻夜讀》
閱讀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