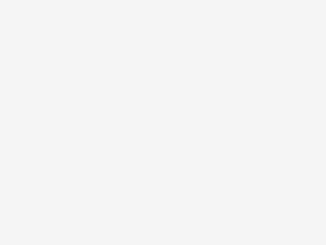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從《養蜂人》《霧中風景》到《永恒和一天》,我們察覺到貫穿安哲羅普洛斯所有作品的、深藏著的孤獨。圖為《霧中風景》劇照。
■本報記者陳熙涵
對安哲羅普洛斯,說任何話都是多餘的。從《養蜂人》《霧中風景》《永恒和一天》中,我們覺察到那種反愛森斯坦蒙太奇的力量:他的詩意長鏡頭,以及那貫穿所有片子的、深藏著的孤獨。
我們熟知的愛琴海文明,是古希臘的戰和血,是狡黠的尤利西斯和暴怒的奧林匹斯之王,是橫穿海洋偷取金羊毛的伊阿宋,是剛烈的女子美狄亞,是憤然與命運抗爭的俄底浦斯。而這些古希臘文明中的英雄,美,崇高,冒險,在安氏的電影里是統統看不到的,他的電影似乎只為追尋一個主題:眾神死後,世界會是怎樣?
今年上影節「向大師致敬」單元,鎖定的大師之一便是希臘電影導演西奧·安哲羅普洛斯。在安氏76年的生命和40多年的電影生涯里,除早期一部未完成的故事片和最後拍攝了一半的遺作外,共創作了十三部劇情長片和兩部紀錄片。大師生前曾將電影劃分為智性電影和感性電影。他說,有些電影是從理性出發的,有些則不。在他所有作品中,《養蜂人》一片是被他親手從智性電影的陣營中「摘」出去的,由此可見它的特別。
電影開始後的第一條字幕,不是片名,不是導演名,而是主演的名字:馬塞洛·馬斯楚安尼。1986年,馬斯楚安尼已62歲,比起拍費里尼《甜蜜的生活》時,他在《養蜂人》中的角色又老又頹又發福,還有些駝背。由他飾演的斯皮羅,是個正在老去的養蜂人。春天里,他的大卡車帶著蜂箱一路去追著各種花開,停留在一個又一個地圖上都沒的地方,淒楚、孤獨、迷茫、矛盾、困惑、沉默、頹廢、敏感,混織在一起,鋪滿在一張皺褶的老臉上。隨著他的老夥伴一個個因體力不支離開了放蜂者的隊伍,他很清楚這一趟,可能是他作為養蜂人的最後的旅行。
在二女兒的婚禮上,他是一個遊離在家庭之外的人,長期出車在外,使他的精神和肉體一直在「在路上」。安哲是那麼善於為作品設置遊離於生命體驗之外的超現實意象:《養蜂人》中,斯皮羅帶著一車蜂蜜遠走他鄉;《霧中風景》中,未成年的兄妹倆對父愛悖論式的尋找;《鸛鳥的踟躇》里那場兩岸相隔的婚禮……這些鏡頭的原創性、想像力和詩性,屢屢擊中觀影者的內心。只要粗略查看對安哲羅普洛斯影片的評論——不管是出自專業影評人之手,抑或業餘的感慨,我們總能發現諸多「附加值」,這些「附加值」,無一例外地與拷問生命的意義相關,與在路上的終極追尋相關,與孤獨地審視個體間的疏離相關。
女兒婚禮那個全家合影的場面滑稽而讓人印象深刻。兒子低著頭,母親看著父親,父親看著女兒,女兒看著丈夫。每個人都在看著心中最重要的那個人,而被看的人卻不知被註視著,無法溝通的情感,在凝視中留在無望的底片上。
在放蜂路上,老斯皮羅遇到一個年輕女孩。她無所顧忌地爬上他的副駕駛座,然後說:「去哪里都行,只要離開這里。」她肆無忌憚住斯皮羅的小屋,吃他買的食物,從他口袋里拿錢,連易拉罐都讓斯皮羅替她開。她從不回報什麼,一切都那麼理所應當,就像孩子從爸爸那里得到庇護一樣。然而,她鮮活的生命力不知不覺注入了他老去的靈魂和身體……
片中這個女孩的名字一次也沒出現。我願意認為,她是生命的隱喻,是這老人正在失去的一切。她有年輕的臉龐,躁動的激情。在他的身邊,她像太陽般耀眼,像月亮般皎潔;她是生命力罔顧一切的衝動,蠻橫無理地闖入我們的生活,毫無理由地支配我們,她讓我們看到希望,又在我們想要抓住時棄我們而去。安哲把一切安排在充滿希望的春天……而四月卻是最殘酷的季節。
終於,斯皮羅與女孩來到一個破落劇場,他們躺在空寂的舞台中央,火車在門外轟隆隆駛過,在這里火車形成的隱喻是徹底的絕望:對女孩來說,斯皮羅是她青春旅途的過客,只是「碰巧路過」;而斯皮羅卻把她的離開,當成了生命的終點。
影片的結尾,斯皮羅掀翻了蜂箱,放走了蜜蜂。它們飛得漫山遍野,一個個白色的蜂箱遠望就像一個個的墓碑。斯皮羅倒下,任憑蜂毒蟄死自己。他的一只手不停叩擊著身下的泥土,仿佛在完成對生命的質詢……
這部攝於1986年的電影和《永恒和一天》有著共同的主題,即人怎樣面對老去和死亡。故事從來不是安哲電影的重點,有些導演的電影會用長長的對白展示自己的意圖,而安哲有安哲的方式。作為「沉默三部曲」之一,《養蜂人》是一首從導演心中溢出的詩歌,憂傷時,他不用眼淚,而是雨落在餐桌上的玫瑰花束,幾乎能嗅到潮濕的味道;離別時,他不說再見,而是老父親一把抱起女兒,給她念童年時曾念過的歌謠,恰到好處的留白給人們留下無限想像的空間。
安哲曾說,我拍的是同一部電影,我所有的影片只不過是這一部電影里的不同章節,要是給這一整部電影起名字,那應該就是「人類的宿命」。他對電影的理念,便是表達人類宿命的語言。
然而,安哲那些充滿詩意的寓言式作品對觀眾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據說他的電影曾讓韓國導演金基德昏睡,醒來後便提前離場。他的電影極度考驗觀影者的耐心,考驗你是否能將電影與娛樂劃清界線。《流浪藝人》在近4小時的片長中只用了80個鏡頭,導演對鏡頭的編排功力發揮到了近乎「變態」的極致:攝影機優雅又不安地掃過大片凝固的風景,穿過空曠的靜物,最後停留在擁擠的人潮。
這從一定程度上折損了安哲影片的「普適性」,故而《尤里西斯的凝視》在1995年的金棕櫚爭奪大戰上惜敗庫斯圖里卡的《地下》而只捧得了評審團大獎。這種建立在複雜調度基礎上的變焦推拉的長鏡頭,在《地下》噴薄而出的歡謔氣質面前,顯得孤絕而落寞。三年後,他憑《永恒和一日》終於摘獲金棕櫚。
截取他13部長片中的任意片段,你會發現那種飽經風霜的華麗和樸素深邃無處不在,安哲讓現實與超現實以一種「作者主導」的方式存在於電影之中。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作者電影」在成就他的同時,也讓他失去了票房的眷顧,安哲無任何一部作品進入院線上映這個事實說明了這點。
對此,他一笑置之。事實上,正是那些行走在票房邊緣的人,成為了書寫電影史的人。正如他所言,「我相信不管在什麼領域,真正的變革都不是由多數而是由少數完成的,即那些例外者。」
>他所有的電影,都是表達人類宿命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