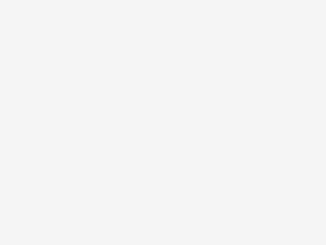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 你想閱讀一篇傳奇性的特稿。它於2007年橫空出世,驚動了整個特稿界——不僅僅是因為它的質量(它獲得了當年《南方人物周刊》「年度特稿獎」),它的題材(少年弒母),而且因為它的第一作者,林珊珊,在那時僅僅是一個實習生。
· 不知不覺,八年過去,作者林珊珊已成為業內著名記者,她將於下周二(3月17日)來到北大新聞學院新傳院105室,作為我們單讀沙龍的嘉賓與楊瀟進行對談。她究竟是如何寫特稿的?八年前她又經歷了那些變化?您可以帶著問題來到我們的沙龍活動,去親自問問她。
· 還要告訴您的是,沒錯,我想我們的確是瘋了——我們在微信上推送了這篇的全文,近一萬五千字。我們理解您或許無法忍耐要關掉它,或者對著螢幕吼太長不看,是的,我們都理解。但是我們仍然想說一句,有些文字值得您這麼做。
(背景介紹:本篇報導來源於真實事件:1991年出生的河南少年張明明跟隨父母到廣州打工,在打工期間,他原來對大都市的憧憬被作為那個城市被遺忘群體的現實代替。他在這期間迷上了上網,不願意跟隨父母再過賣燒烤的生活。種種不適應及心中淤積矛盾最終爆發出來,最終殺死了他的母親。)
1殺掉父母,這個想法盤旋了兩個月
這個想法在他腦中盤旋了差不多兩個月。
「我想,只有殺了我的父母,才能讓我多年積累的仇恨得到釋放,讓我真正地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
1991年11月25日,陳菊生下了他;2007年6月12日,他將陳菊打暈、掐死,然後割喉。
其間,陳菊打開大門慘叫一聲,但門很快又被關上。那就像荒林里一聲絕望的鴉叫,一切又恢復了寂靜。
這幽暗的小巷的深處,有一個拐角,幾棟四層高的樓房圍成一口天井,張明明的家在這兒。抬起頭,天空依舊是一條狹長的線,被錯綜複雜的電線切割得支離破碎。一米多寬的小巷兩邊房門緊閉,垂吊的女人內衣透著濕氣,牛仔褲則似乎長年掛在一邊,一動也不動。還有一個個小口子,連接更小的巷子,有時候,一個安靜的小孩跟著一個女人拐進去,或者,一個謝頂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睜大眼睛瞪著過往行人。聲音從遠處隱約傳來,光亮在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親張柱良就從這個巷口逃了出來。
2父親:艱難的謀生
張柱良抽著紅雙喜,手微微地顫抖,煙霧輕輕裊裊懸浮著空中,他的目光飄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數十年後,有一天,我們也會經受這樣的疑問,你收獲了什麼。張柱良的答案是:賺錢。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來到廣州。想像中的廣州很繁華,但不是那麼回事。站前路那家大酒店當時還只是一個大土堆。下了火車,我看見到處是賽馬的宣傳,湧動的人頭。我擠在人群中尋找大哥張光榮,來之前,他對我說,下了車說找河北老張,他們都認識我。可當時大哥在花都。當晚我睡在韶關大廈下面的廣場,半夜一拳頭打在我胸口,我驚醒過來,丟開旅行包逃走了。接下來的兩天,我在車站晃來晃去,檢查人員盯著你,你吐口痰,丟一片紙屑,就跑過來,罰款十元。我僅有的四十塊錢很快被罰光了。我只能幫人提提行李,兩三天就混過去了。
我跟隨大哥賣黃牛票。那時火車站的生意真好,天天都像春運。那些人排著長長的隊伍,到了窗口,售票員就說沒票了。我們就湊上去問,老鄉,去哪的,幫你買票。我們很容易拿到票,他們售票的每天回家兩個口袋滿滿全是錢。僅做了兩三個月,我就做不下去了,我總問到便衣,而且,騙人這事我幹不漂亮。當然,最無恥的不是我們,而是那些敲詐的。他們奪過旅客捏在手里的票,「給我一百塊,不然把它撕了。」
接下來將近十年,我幾乎都在當保安,跟過服裝場、酒吧、夜總會、地下賭場……
1996年,你知道,到處都是歌舞廳。那時我在沿江路一家歌舞場當保安,聖誕節那晚,門票200塊錢一張,等著跳舞的人排著長隊擠在陽台上。那一年前後,我認識一群流氓。我們四五十人自稱河北幫,幫人看場、收債和打架。老大一叫集合,我們就掄起水管、排骨刀,湧上去往人家背上胳膊上亂砍。有吃有住有玩,我們都很樂意。我們被抓進派出所無數次,又放出來。
當時,大哥承包了幾家酒店的洗碗活,幾十個工人都是去火車站找的那些沒飯吃無家歸的人,提供吃住,一個月350元,大哥每人賺上一百。老李是這些流浪兒中的一個,後來他結識了賭場總經理,就介紹我去當保安。老李後來失蹤了,那時我就知道,我們這些人都是不長久的。
那是1997年,一個地下賭場每天賺上十幾萬。只要我站在那里,就會忍不住想賭。結果薪水剛發,一眨眼就輸光了。一想到該寄錢回家,我就特別緊張。到了年末,賭場聞風警方要大規模打擊地下賭場。我們就自行解散了。
1998年,我在一家樓盤終於當上正規的保安,到了2001年,還混上了保安隊長。可是,不久,開發商與物業分家。我又失業了。
我重新回到賭場,這下賭場都是先進玩法了,最主要的是玩老虎機,還有一些黑網吧。一次警察來檢查,我們立刻趕走所有的少年,但還有一個少年玩得入迷怎麼也不肯走,就被我們打了。再後來,他的媽媽闖進來了,操起凳子往電腦砸過去,我就罵她:「是你兒子自己要來的。我們又沒強迫他。」
2003年,我開始和老婆在廣州賣燒烤,到了2004年,老婆說兒子也大了,讓他來幫忙吧。於是,我們一家三口住在瑤台,相依為命,靠賣燒烤為生。
3賣燒烤的日常生活
這是瑤台,離廣州火車站不遠的城中村。一座不夜城,夜幕降臨,它的黎明剛剛開始。濃烈辣椒味混著啪啪炒菜聲彌漫在小巷里。夜晚九點鐘,才起床不久的張柱良踩著他的黑色28吋自行車出發了。
車後架上躺著一個泡沫箱,里面堆著雞翼、雞腿、羊肉串、秋刀魚……盒蓋上倒扣著兩張小凳子,茄子、菲菜陷在里頭。緊跟在他後面的,是兒子張明明,騎一輛26式自行車。8點半,他準時從網吧歸來,把一張沾滿油污的長方形小桌子和燒烤爐綁在車架上。此時,陳菊上了香求完平安,關上燈、鎖好門窗,也出門了。
一家人在三元里一帶賣燒烤,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晚上九點鐘出檔,凌晨三四點收檔,然後睡覺。中午醒來,切肉、洗菜、調料、串羊肉串。晚上再睡上兩個小時,又出檔了,日復一日,如今已是第五個年頭。
這一天是2007年6月11日,只是時間洪流中一個不起眼的小日子,卻足以拒絕這個家庭繼續前行。
4站街女
張柱良往左拐出小巷。這條街總是這麼熱鬧。穿開檔褲的小男孩在路中間嗑瓜子,鼻涕滴答、懵懂地看著你,中年男人圍成一桌桌喝酒、搓麻將,小攤販的玉米、番薯散發出熱騰騰的香氣,手機店里各種音樂混雜著人聲車聲孩子的哭鬧聲鼓搗著人們的耳朵。
在路的盡頭,他向右拐,那是一條陰暗狹小的路,只能推著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這條街還很安靜,到五點半,每走幾步就可以看到一個站街女。
有時她們抓住他的手,「要不要?」他罵道,「每天都看見我經過,還抓!」他厭惡地甩開手。
可有時,他也心生同情。一天中午,他在街上亂逛,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穿著短褲,黑色男裝背心,呆呆地站在前面。突然,她大喊大叫,闖進檔口,拉住一個男人的衣角,哭喊著:「爸爸,別不理我!」那男人用力地踢開她,她又闖進另一家鋪面,又被狠狠地踢在街上。他看著她,真想把她送到派出所。但很快,他打消了這種念頭。這些人都認識他,很多雙眼睛盯著他。他只是想著,這個倔強的女孩子,一定是想不開,受不了,被生活逼瘋了。
要是軟弱一點的,就屈服了,不久後還會招來同鄉姐妹。她們或許在火車站流浪、或許是離家出走,然後被騙到一個地方,賣淫。這個街頭,他撞見過七八個神經錯亂的小姑娘,有的亂跑亂叫,有的癡癡望著天。此後,便永遠地消失了。
幾分鐘後,一家人擠出瑤台村,來到廣園西路。一條寬闊的街道就在腳下延伸了,到處都是汽車,高架橋上的疾馳而過,地上的擁擠混亂。
5少年張明明盼望著不開檔
他們橫穿過車流。沿著三元里大道一路上坡,沿途是嶄新的酒店及貿易公司。張柱良吃力地踩著,他忍不住想,這滿大街的人誰看得起我呢?
這天中午,他穿著黏乎乎的大褲頭,趿拉著拖鞋,提著肉和菜從市場回來,朝一個30多歲的男人點點頭。那個男人頭髮齊整,皮鞋鋥亮,禮節性點完頭又和周圍的朋友談笑風生。
他決定,別再和他打招呼了,顯得自己多卑微。他想,那男人一定輕聲地說,他是賣燒烤的。「賣燒烤的!賣燒烤的!」十年前,這男人和他一樣,是廣州一家夜總會的保安。他被這男人刺痛了,但他不停告訴自己:不能停!不能停!
2003年以前,他是窮光蛋,倒霉鬼。一做生意就虧得血本無歸。
在河南老家,他賣過鹵豬,卻遭遇了「五號病」,沒人敢吃豬肉了。豬肉堆在家里讓人發愁。再後來,看到別人倒賣棉花發了財,也就偷偷地收購一些拿去賣。朋友開著改裝摩托車,他坐在一車軟軟的二級棉花上,喜滋滋地想著這回該賺上一千塊。可到了隔壁鎮的工商局門口,爆胎了。於是車子被工商所帶走。後來,他橫著膽再幹一回,結果又讓鄰縣的工商局給抓了。
他媽媽說,會做生意才算男人。現在,他賣燒烤,每晚能賺幾百塊,他成了五兄弟中最有錢的那個。
多虧了這小生意,家里才建了樓房,那是給張明明娶老婆用的。堅持,堅持,再過上兩年,他將做爺爺,妻子將做奶奶,那時就可以享清福啦。
他告訴自己,他是一家之主,他要在前面領跑,其他人要跟著他跑。
張明明呆呆跟在父親後面騎著。他盼著下雨,下雨就不用開檔了。去年,他總是找比他大兩歲的老鄉、同是賣燒烤的周周一塊玩。一次去擺攤時,天色忽然變暗,大雨將至。張良柱踩上車,他卻往相反的方向上網去。到了燒烤點,張柱良發現兒子沒跟上來,立刻打了電話給周周。
「明明在你那嗎?」
「沒呢,叔叔,快下雨了,今天就別擺了吧。」
「不用騙我了,他一定在你那里。」
周周只得把電話給了明明。
「你馬上給我過來,我是一家之主,我說了算。」
他嗯了一聲,掛了電話,踩上車走了。
6「廣州很繁華,但我很孤獨。」
「從我被媽媽帶到廣州那天起,我仿佛就於(與)世隔離了。」
2004年9月,張明明在河南老家讀完4年級,陳菊決定將他帶到廣州。
臨走前,張明明拖著堂妹靜靜的手說:「過去的明明已經死了,現在的明明已經不是以前的明明了。」
他曾來過廣州,在一家外來工子弟學校就讀,一個學期的學費大約是1200元。
有時,張柱良看到他渾身淤青,但兒子總說是摔傷的。「為什麼身體前後都有傷呢?」兒子便不再說話。
至今為止,也沒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個學年以後,他對母親說想回河南了,他離開了子弟學校。今天再去那里,找不到他的檔案,找不到他的照片,找不到認識他的老師,和他生命有關的痕跡,全都消失了。
他似乎只有網路了。他有個網路好友叫小白,他叫她姐姐。
「我很悶,我沒有朋友,也不會講話。」
下午六點到八點半是他的上網時間,「可是,爸爸媽媽卻不允許我去上網,讓我用上網的時間多睡會。我覺得這是在禁止我的自遊(由)」。
「廣州很繁華,但我很孤獨。」
7曾想面試總經理,「就憑我的智商」
張明明跟著父親往前騎,將瑤台拋在身後。旁邊的瑤池酒店依然霓虹閃爍,漂亮的服務生在門口排成兩排長長的隊伍,每有客人進入,就齊刷刷地彎腰鞠躬。
去年五一,張明明看見一個比這個更高級的酒店,門口貼著招聘啟事,上面寫著招一名經理和幾名服務生。那時他陪最要好的堂哥阿強在廣州找工作,他拉著堂哥湊上去,指著第一行:
「哥,趕明兒我去面試總經理。」
「就憑你?你什麼也不會,憑什麼去當總經理。」
「就憑我的智商,過幾天當給你看。」
來廣州之前,阿強想像這個城市漂亮,乾淨,就像電視里演的一樣。要在這謀上一份工作就好了。中午下了火車,他跟隨著叔叔張柱良,一路來到瑤台。第一次走進這條小巷時,他就想,我再也不要走這條街了。穿過幾條陰暗的小巷,阿強來到叔叔的家。張明明還在房間里睡覺,阿強敲敲房門,是表弟小狀來開的,小狀大聲說,「明明,明明,快起床,你哥來看你了。」兩年沒見面了。張明明睜開眼,慢慢站起來,聲音很輕:「哥,你來了。」
「我心里有點失落,他不是興沖沖跑上來說,哥你來了。」阿強說。
他眼前這個小男孩變了,滿臉痘痘,悶聲不語。
張明明其實是很開心的,只是不愛說出來而已。小時候,他被欺負了,堂哥一定是第一個幫他去討回公道。張明明不愛打架,別人打架,他就站在一邊看,不動手。不過,要是給人欺負了,那是一定要報復的。那年他12歲,被同學欺負了,他氣沖沖跑回來,脫掉上衣,掄起棍子就往人家家里跑,被人家打回來了,他才叫上堂哥,堂哥又叫上他的哥們。
接下來的日子,他晚上照常出檔,白天就陪堂哥四處找工作。
有一次,經過一條黑巷子,一只只碩大老鼠在他們面前竄過。
「真不想走這里。」阿強說。
張明明走在前面,沒有說話。
來在大路上,張明明突然說:「哥,廣州和你想的不一樣。」
8「哥,我就是要做曹操那樣的人。」
「這麼晚才回來,要耽誤生意了,幹活去!」張明明踏進家門,陳菊劈頭就罵。他不耐煩地說,「很累了,讓小狀幹去。」他把門用力甩上,倒頭就睡,陳菊在門外嘮叨起來,「連小活都幹不好,怎麼掙大錢!」
但這一天,他心情頗好,他對阿強說:「我要寫兩本書,到時請你當男主角」。
隨後唱起《曹操》:
「不是英雄不讀三國,若是英雄怎麼能不懂寂寞。
獨自走下長坂坡,月光太溫柔。
曹操不羅嗦,一心要那荊州,
用陰謀陽謀明說暗奪,淡薄。
東漢末年分三國,烽火連天不休。
兒女情長被亂世左右,有誰來煮酒。
爾虞我詐是三國,說不清對與錯。
紛紛擾擾千百年以後,一切又從頭。」
他把自己的歌聲錄在阿強的手機上,一遍又一遍。他已經很久沒說過那麼多話,也沒這麼開心過。嗓子很快就累了。
中途休息的時候,他對阿強說:「哥,我就是要做曹操那樣的人。」
「為什麼不做呂布呢,呂布最能打,身邊還有個美人貂嬋。」
張明明想了一下:「不,還是曹操有勇有謀。」
又對著手機唱起來。
聲音有點大,張柱良啪啪地打著他的房門。他們不敢再出半點聲音了,蓋起被子趕緊睡覺。
9「他要寫劇本,還要請成龍拍。」
張明明的確寫過兩本小說,一本叫《雪山劍派》,一本叫《十八金甲將》,在他心中,這是他夢想起飛的舞台。
一天晚飯時,小狀迸出一句話:「咱們家出了個作家啦!」
「什麼作家?」父親很好奇。
沒等張明明回話,小狀接著說:「他要寫劇本,還要請成龍拍。」
父親一下笑了:「好呀,寫了給爸看,我雖然不會寫,但還是會看的,要寫就買筆買稿紙去,好好地寫。」張明明點點頭,靜靜地吃飯。
不久後,一天夜里,客人散盡,一家人收拾著檔口。在三元里紀念碑旁邊,張明明發現了一張被丟棄的桌子,他將桌子掄起放在車架後面,搬回家,擦得幹乾淨淨。接下來幾天,他安安靜靜地趴在桌子上寫作了。
傍晚六點鐘,一家人吃過了晚飯,父親躺在床上半閉著眼睛,張明明挪過去,將兩頁稿紙遞給父親。
「嗯,錯別字很多,但情節還不錯,好好寫下去。」
張明明靦腆地笑了。
一年之後,張柱良回憶起這幾天,他的臉上總掛著微笑,這幾乎是他們父子最溫馨的時候,那時候,張柱良傍晚不睡覺了,專心看兒子的小說。除了找資料,張明明也很少上網了,專心寫小說。
就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了湖南的網友小白。
「你是做什麼的?」小白問。
「我沒做什麼,在家寫小說。」他很驕傲地回答。
「好厲害哦,寫得怎麼樣?」
「我爸說不錯。」這應該是這兩本小說的唯一讀者了。
……
「你知道成龍的郵箱嗎?」
「我不知道,你可以到網上查查。」
「你有郵箱嗎,能不能借我?」
小白將她的郵箱借他了。後來,他找到了成龍的郵箱地址,成天給成龍寫郵件。
2006年9月27日,他在新浪開通了自己的博客——名字叫「等待夢想」。
10他在博客上寫:各位記者你們好,向你們報社連載欄目中投稿,有什麼意見可以給我留言
張明明每兩三天就拿一集給張柱良看,但父親發現他的字越來越潦草,情節越來越混亂。
二十多天,兒子寫了十多集。有一天,張柱良說:「我不知道你在寫什麼,肚子里沒墨水,自然是寫不好的……你這是沒先學走先學飛,還是從小文章寫起,好好研究《廣州日報》那些小文章是怎麼寫的,然後去投稿。」
一天清晨,他和周周去進貨,他問周周:「知道廣州日報在哪嗎?」
「知道,那有我很多賣燒烤的朋友。你要幹嘛?」
「帶我去。」
終於到了廣州日報社,他停下了車,抬頭望著那幾個紅色大字。
「你來這做什麼呢?」周周問。
「我想投稿。」
「哪有那麼容易呀?」
張明明沒有回答,只是笑笑。
「進去看看吧。」
張明明看看守在門口的保安,搖搖頭,騎上自行車走了。
2006年12月6日17點14分,他在博客上寫道:廣州日報的各位記者你們好。我是向你們報社連載欄目中投稿希望可以上報。有什麼意見可以給我留言。
「雪山劍派//////作者<張明明>武俠小說,第一集..天玄地門一」
下面沒有了。
11小說的往事被2006年的尾巴甩開,張明明再沒提過
每次上網,他就問小白,有我的郵件嗎?
沒有。
一天的燒烤忙完了,一家人圍在桌子邊休息。
「作家,成龍給你打電話了嗎?」小狀逗著明明。
「不久他就會給我打電話了。」
父親心里暗暗發笑,於是故意問道:「他怎麼給你打電話?」
張明明指了指父親別在腰間的手機:「就打叫燒烤這個電話。」
「那你叫成龍晚上9點後才打過來,白天我們可接不到電話。」父親哈哈笑著。在城中村,他們花360元租的房子里,手機是沒有信號的。
張明明不吭聲。
這些關於小說的往事被2006年的尾巴甩開,張柱良再沒聽過,也沒向兒子打聽過。
張柱良恢復了晚飯後的睡覺,張明明又恢復了上網。
2006年底,他和父母回老家過年,這是他來廣州兩年後第一次回家鄉。當晚,他叫上最好的朋友佳林、李闖直奔網吧,玩一個叫「半條命」的遊戲。凌晨,他不想回家,和佳林跑到廟里頭,折了一小捆樹枝生火取暖,火苗一下躥了一米多高,他倆趕緊把火熄滅,撒腿就逃。
這年春節是這幾年中最好的時光。18歲的堂哥阿強結婚了,有了自己的家。他不再上網玩,他要更努力地賺錢。
20多天的假期轉眼過去,來廣州前,張明明對阿強說:「哥,我不想去廣州了,我想在家里打工。」哥哥幫他向他母親說情。但母親說,再說吧,再做一兩年。
再說,再說到什麼時候呢。
12半年時間,他就像一只老鼠,在深夜獨自穿梭在城中村
張明明跟隨父母再次回到廣州。
他漸漸不和李闖來往了,這個童年時的夥伴在老家的公車上負責拉客,張明明疏遠了他。「他變了,」他說。小狀過完年就到天津去打工,愛說話的孩子一走,這個家庭也越發沉悶了;去年同他一塊進貨、打籃球、跑步、上網的周周開了燒烤分檔,有了摩托車,有了更多朋友,也更忙了。
現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父母。
他像是生活在時鐘上的秒針,被其他兩根牽動,日復一日地幹著同樣的活:凌晨四點幫忙收檔回到家,然後踩40分鐘的單車去和平西路的凍品市場進貨:四十斤雞腿、二十斤羊肉和火腿。他總是獨自穿梭。
他上網越來越頻繁了。
網吧藏匿在鄰巷一家小賣部後面,張柱良在兒子和老鄉的一次對話中得知網吧地址。他走進去,逼仄的空間擺放幾台電腦,坐滿了人。張明明弓著背雙手交叉快速敲打鍵盤。他推推他,兒子扭過頭,兩人相互看了一眼,面無表情。
13在遊戲中他不再是一個賣燒烤的
父子倆一天說不到五句話,幾乎連架都沒吵過。他們的對話只有三種可能:一是父親自上而下的命令,二是兒子自下而上的匯報,三是上網前借口與反借口的對峙。
下午五點半是家庭的晚飯時間。妻子和兒子則在小短凳坐著,張柱良則坐在床上,俯視他們。他喜歡這種感覺。
張明明注意著父親的一舉一動,父親一走開,上個廁所或洗個手,他趁機就溜了出去。有時父親那兒也不去,就在床上躺著。
他的QQ上有72個好友,聊天讓他找到在孤獨之前的那種快樂,這種孤獨在他來廣州後死死纏住了他。他還可以在遊戲中做另一個自己,不再是賣燒烤的,而是一個除暴安良的警察或者是一個拉風的卡丁車車手。這兩種快樂讓他在令人厭煩的生活里有一點放鬆。
「我去打個電話給朋友」,「我去買東西」……他低著頭等張柱良回話,張柱良沒吱聲,半閉著眼看他。他慢慢抬起頭瞅瞅父親,又低下頭。
每當父親就說「不行」,他就咬緊嘴唇,扯著衣角,站在門口扭動身子。而當父親五指輕輕一揚,他立刻彈了出去。
父親知道他去上網,他也知道父親知道。
14他在床頭刻下兩個字:仇、恨。
有時張柱良也會發怒,把飯碗往桌上用力一按,指著張明明,一字一頓地說:「從今天開始,不許你再去上網。」張明明不敢吭聲,放下飯碗往房里跑,啪的一聲把門關上。母親去敲門。
「什麼事?」他沒好氣大聲說。
「拿東西!」
「明天再拿!」
張柱良親自出馬,咚咚咚敲著門。
「什麼事?」
「拿東西。」張明明連忙開門,又躺到床上去。
第二天,張明明又在屋里團團轉,不時觀察父親的動向,如果無機可趁,便支支吾吾開始找借口。
借口找多了,乾脆赤著上身穿著短褲跑出去。張柱良想,他總不會赤身去上網吧?便沒叫住他。但他真的上網去,直到燒烤攤開檔才回來。張柱良對他說:「上網也總得穿上衣服吧。」他不回答,走開了。
借口仍然需要找。一次,張明明吃過晚飯,對父親說:「我要去買鞋墊。」父親說:「行,五分鐘後回來。要是想上網,就別找借口。」他靠在門上,歪垂著頭,一動不動,也不吱聲。陳菊看著難受,推著張明明說:「行了行了,你快走吧。」
張明明氣得直往牆上捶打。這天晚上,他在床頭刻下兩個字:仇、恨。
啪,啪……這段時間,他緊閉的房間里總是傳出打火機的聲音。
15張明明哪一點最像張柱良?記仇。
6月11日晚上九點半左右,中港皮具城。大廈緊閉,白日里鏘鏘的皮鞋聲、貨物運送的嘩啦聲全然退去。
往前走,一條冷清的街道伸入黑夜,兩邊停著十幾輛腳踏貨運車,搬運工無所事事坐在上面。左邊是一個地下停車場,各式各樣的小轎車從底下拐出街頭,每天,這一家人就從這街頭拐進來。
此刻,燒烤爐火生起來了,停車場邊的空地也漸漸熱鬧起來,生意還是如同往常紅火,張柱良不停烤著雞腿,魷魚……張明明馬不停蹄地遞生肉,送外賣,陳菊收錢、找錢,招呼著客人,對久等的客人道歉。
這一天,他們並不愉悅。
張柱良跟陳菊商量:咱們開個小飯館吧,四處躲避城管討好客人,多窩囊呀。陳菊說:給我乖乖把這生意做好,你現在能做什麼?你能賺大錢麼?他不再說話。。
陳菊深諳和氣生財的道理,看車的保安老盧說,這里的人誰敢說她一句不好?她總在張柱良耳邊嘮叨,千萬要忍住!要忍住!張柱良也總按住張明明的火氣,給我忍著,人家有錢有勢,把你整死還不容易,等咱不幹了,看誰不爽就打誰。
張明明哪一點最像張柱良?他眼光冰凉,吐著煙圈,輕輕飄出兩個字:記仇。
16記住得罪過他的每一個人
張柱良記住得罪過他的每一個人。
一個是大廈的小保安,那一次城管沒收他的桌凳時,本沒注意那箱生肉,小保安卻提醒了城管。張柱良看得咬牙切齒:「你這小保安也太自不量力了,想這樣要制服我。」他請了保安隊長上酒樓吃飯,保安隊長拍胸脯保證,這種事絕對不會再發生。小保安真的來道歉了,但這還不解恨。
另一個是居委會的。那個30多歲的湖南人有一天跑去對張柱良說:「你們這樣擺攤不行。」張柱良沉默地看著他。「不過——」他又繼續說:「我跟主任說了,關照一下你。」張柱良說,「謝謝關照,以後城管來了,可要麻煩你通知我。」「一定,一定。」以後,每隔兩三天,他就拿一瓶碑酒坐在他的檔位,張柱良總得給他添酒,烤雞腿、羊肉串。城管來之前,他果真放出風聲。他有時也借錢,但從來不還。
張柱良憎恨這兩個人,他總在想:要是哪一天我先不幹,老子一定把你們狠狠揍一頓。當然,那個居委會的,要先還錢,再揍。
17兒子總是呆呆的
兒子總是呆呆的。張柱良從來不知道他的腦子里裝著什麼。
賣燒烤時,張明明時常一人自言自語,「為什麼趙子龍打不過呂布呢?」他喜愛《三國演義》,聽到有人要重拍三國,他在博客上寫:「幹嘛要重派(拍),有人跟我說‘沒劇本’聽的後我很難過,我空有好劇本可就沒人知道,經典再重派就不好,哎再想起三國真是‘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真感人。」
他幻想自己能去演趙雲,「我的形象也符合啊,哎,我的劇本就是沒人看。」
客人罵他他從不還嘴。
他送外賣,不停催著父親,「外賣的先烤!外賣的先烤!」
外賣送晚了,是要挨罵的,有時候還拿不到錢。
陳菊則擋住他,「不行不行!這里的先烤!」
旁邊的客人總一遍一遍地催。
每次送外賣之前,他總要計算好要找的零錢,有時候直接將零錢和外賣一同遞給人家就回來了,母親問:「錢呢?」哦,他忘了拿。他的算術從小就很差。
那時他才小學一年級,張柱良難得回一次家,翻起了他的作業本,滿是大大的紅叉。他很氣憤,怎麼「三九二十七」都算不出來!他逼著他再算一遍。他直冒汗,但怎麼掐手指也算不出來。父親怒了,啪啪給他兩個耳光。孩子站起來,不哭不鬧,含著淚水直瞪瞪盯著父親。
這個眼神,張柱良終身難忘。看得他難受,害怕。
18「你喊打,我就打!」
這天晚上,一幫潮州客人喝醉了酒,嘔吐了一地,還摔爛了酒瓶,張柱良趕緊把地掃乾淨。但他忘了給他們燒茄子。客人大聲說,給我快點,不然不給錢,大夥起哄大笑起來。
他低聲罵道:「媽的,敢不給錢就揍你。」
張明明把刀往桌上一扔,對父親說,「你喊打,我就打!」
陳菊責罵他們:「你們不要再說了,別讓人家給聽到。」
客人最終給了錢。
凌晨三點多,天空下起了小雨。周圍一片寂靜,只有快速馳過的汽車發出沉悶的嗚嗚聲。父子倆騎著單車先走了,陳菊本該坐在張柱良自行車的橫杠上。但這會,她一個人在後面走著。保安老盧遞上一把傘,她沒有要,她說:「我沒時間還你。」
她是真的沒有時間還了。這將是她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晚。
19「她會用一種討厭和憎恨的眼神瞪著我看,她還是我媽嗎?」
陳菊喜歡當著張明明的面對張柱良說,「你這兒子,靠不住。」她並沒意識到,這對張明明意味著什麼。
「在爸爸限止(制)我自遊(由)的同時,媽媽也不喜歡我天天跑出去玩電腦……媽媽卻一天到晚說我這樣不行那樣不行,有時我頂撞她兩句她就不出聲,只是她會用一種討厭和憎恨的眼神瞪著我看,我看到她這眼神的時候,心里一陣酸痛,眼里的淚水都要流出來,我強忍著把它壓回去了。事後我想她竟然用這種眼神看我,她還是我媽嗎?」
慢慢地,張明明適應了她的這種態度,只是每當她再看他的時候,他的心里還是會有些酸楚。
在他很小的時候,陳菊帶著他長大,可她愛打牌,總是奶奶弄飯。2004年,在奶奶動完手術後的一天,張柱良一進門便朝著陳菊摑上一掌:「媽媽看病剩下的錢,你竟敢要。」陳菊哭鬧著往外跑,一邊喊著,「是我的錢,我就要。」他真抓住她繼續打。這時,張明明擋在中間,「別打了別打了。」
之後,張柱良對兒子說:「現在你奶奶走路都走不穩,你媽媽還向她要錢,這完全不對。」他點點頭。
20「我要走自己的路,過自己的生活」
張明明決定要實施他的計劃了。此前,他想過三次,這回「就算是違背自己的心意也要做」。
「6月7號那天,我一天沒睡就是想趁令(今)天這個機會殺了他們,中午12點的時候我爸爸起床了,先去市場買貨,他買完貨回來後,媽媽又去買東西了,那時,在里屋的我不知道在外面的是誰,心想:‘管他是誰呢,瞄準機會就下手。’我打開屋門,來到大廳看見爸爸正在切羊肉,我洗過臉後,在他後面梳頭,心想:‘先殺了他再說’,然後我從我下面的玻璃櫃中拿出了準備好的鐵棒,我舉了起來想打他的頭,可是當我要下手的時候,手卻動不了,心里也在想他是爸爸呀,我要殺的是爸爸呀。最後還是沒下手,事後我便想用鐵棒打頭,太狠了吧!那是你老爸啊。」
張柱良後來看到這根鐵棒了,他那時生氣地說:「誰把它放到我床邊了。」誰也沒回答。
「讓他們怎麼安穩地過去,我先想到的是迷藥,可以讓人很快地睡著。於是我到藥店里問:‘有沒有什麼藥,人吃了可以很快地睡著?’藥店里的人買(賣)給了我兩片睡覺的藥,我對這藥的信心(不)足,想試一下。我把藥砸成粉放在了水里,結果水一下就變渾了,我喝了一口味道還有點苦,心想:‘這水我爸媽怎麼會喝呢’。
「於是我放棄迷藥,決定還是打昏他們吧。沒想到我喝了一口那水,很快就睡著,這(第)二天醒(來)才覺得這藥真歷(厲)害。
「我走出屋,看見爸媽都在做事,我也就做我的活,過了一會後爸爸要出去買東西,我想這又是一次機會不能放過。
「爸爸走後,我裝做(作)拿(東西)走到媽媽身後,從我房間里拿出了我先就準備好的木棒,本想也打她的頭,可是還是下不去手,後來我就放棄了。
「幹完活後我在房間問自己,‘你是想就這樣的一輩子,還是想過自己的生活,’我回答,‘我要走自己的路,過自己的生活。’
「然後我的腦子里就出現了怎樣殺死他們的場景,我對自己說:‘下一次絕不能放棄’。」
21「他發瘋似地朝我猛砍」
6月12日,周二。當天《南方都市報》的氣象新聞標題為:《暴雨只是中途休息》——「昨天傍晚,一場激烈的大雨導致廣州難得的多雲天晚節不保。更麻煩的是,遇害來得特別不是時候,淋息了下班人的回家熱情。今天,廣州還將有陣雨突襲,不過討厭的還在後頭,雨水只是中途休息,明天它又將卷土重來。」
這則新聞把「雨還來得特別不是時候」,誤寫成了「遇害來得特別不是時候」。
6月12日下午,將近4點,張柱良提著魚從市場回家。
你媽媽在哪里?在廁所。他十分平靜。我把魚放在廚房,走向廁所,他媽媽平時上廁所從不關門,這一次卻半掩著,並且關著燈,但我沒多想,推開門,見她媽媽躺在地上,我心里害怕極了。我往後退,這是怎麼回事?
我只想到兒子了。我慌亂地往廳里跑,直喊著明明,到拐腳處,這一秒半時間,我來不及思索,忽地一把菜刀猛向我劈來,緊接著看到兒子兇狠的臉。他發瘋似地朝我猛砍,肩上,脖子上……一共四刀,我一片空白,本能地把他按在床上,搶過他的刀,我的血噴了兩米遠,滿牆都是。刀被搶過後,明明一下子安靜了,恢復了正常的表情。
我害怕極了,只想往外跑。我打開了門,明明又用力把門關上,大聲地喊,爸,我沒得回頭了。我什麼也聽不進去,只想跑,把他推開,逃了出去,他追上來,抓住我的手,邊喊著,爸,你聽我解釋。我把他推開,只是淒凉地說,什麼都聽你說。
22我的老婆死了,被兒子殺的
張柱良只想逃命。他往下逃,往亮處逃,沒命地逃。
他一只手捂住臉,血汩汩而流,透過指縫,染紅了衣衫,染紅了巷子。
他一點也不覺得疼,他終於逃出這陰森小巷,沖進小賣部,抓起電話撥了110,那婦女抱著小孩,嚇得直後退。
他跑去對面的巷口直喊「大哥,大哥」。沒有回應。
他又回頭打了120。他走進去,女人驚恐地望著他,指了指在外面的被血浸染的電話。他回頭望望巷子,他害怕極了,張明明會不會舉著菜刀紅著眼殺出來。誰知道呢?
他朝賣燒烤的相反的方向跑去,跑向一條更大的路。他用盡全身力氣跑著,可好像身體凝固了一般。他只覺得眩暈。我是在發夢嗎?他不停問自己。
這條大街的人他都認識。
我的老婆死了,被兒子殺的。
偌大的街上只有他了,人全都退到了兩邊,遠遠地望著這個悲慘的男人。他感到這里如此陌生模糊,他聽不見任何聲響。忽然,一個女人尖叫了起來,「快救他。」之後,又是一片寂靜。他蹲在路邊,他感到血就要流幹了。警察終於來了,他走向警車,警察攔住了他。他又蹲下了。
23張明明打消自殺的念頭
「他是去報警,我該怎麼辦?……跑吧,那時我只有跑了,樓下不能走只能去樓頂。」
到了樓頂後,張明明想過自殺,但這個念頭很快被打消。
「我怎麼能死呢?」
「我不能死。」
張明明在各個樓頂翻來跳去,就像這幾年,他在河南與廣州之間來回輾轉,就像他在出租屋、燒烤點與凍品市場之間千回百轉,就像各種夢想之間不斷遊移飄動。看了《羊皮卷》就想做推銷員,打了遊戲想寫小說,聽了《曹操》想做曹操……可沒有一處屬於他。
他從小就喜歡說夢想,「每個人都有夢,有夢的人活著才不會孤獨,才有動力。追夢的過程是艱辛的。就是追不到,也沒有百火(白活)。只要(有)你的夢是你的一切。我要給自己創造舞台創造機會。永不放棄。」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他總和好朋友佳林逃課跑到學校旁邊的大樹下談夢想、打彈弓、翻筋鬥。佳林記得眼前這個好夥伴有遠大抱負。他真喜歡張明明。他是一個父親早逝、跟隨著母親改嫁而來的外地孩子,飽受欺負,被打得頭破血流,那會兒只有張明明送他去衛生所,幫他打跑那些愛欺負人的小孩。
冬天到了,河里結起了一層冰,一群小夥伴想在上面行走,張明明說,我走前面。最後,他掉下去了,他們用幹樹枝把他撈上來。
他也邀請其他朋友到安靜的地方談人生談理想,但他們只喜歡談打架的經歷。他們問他,「你的理想是什麼呢?」他擺擺手,「說了你們也不懂。」
有個賣燒烤的女孩,陳菊總想撮合他們,你看人家那女孩多好,又漂亮又能幹。一天早晨,阿強和他、小狀去吃早餐。小狀偷偷指著那女孩:「哥,你看,就是她。」
張明明瞪瞪他:「真多嘴。」
阿強看看她,「長得真不差。」
「真是的,不漂亮,不漂亮。」他連忙說。
「如果差不多,就跟人家說說。」
他笑笑,不說話。
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
逃上樓時他忘了拿錢。他的桌子上,有大大小小的盒子,里面放有一條項鏈、小說草稿、一部MP3、一張平平整整的印著「李師傅山東風味鍋貼」的優惠券。2005年他生日時,一家人到那里去吃飯,他們吃了烤羊腿。走的時候,櫃台送了一張優惠券,父親隨手給了張明明,當時父親只想,下次再來都不知是什麼時候了。
MP3是親戚送的。張明明總是隨身聽著,有一次,父親隨口說,你怎麼總一個人聽呀。隔天,他買了兩個小音箱,他播好音樂就走了。陳菊說,你看,你兒子多孝順你。
可惜他永遠都聽不到她說這句話了。
凌晨零時許,他從樓上下來,慢慢走在路上,他並沒有表現出驚慌。
三名便衣上前將他抓獲。
24後事料理完,張羅婚事
門外這個埃及人彬彬有禮,但他有可能是個殺人潛逃犯,他可能沖進來砍我,報警,就可以抓住他,抓住他……
張柱良差點就打110了。
他整夜不敢入眠,聽著門外的一舉一動,他整夜整夜地臆想,聽到半點聲響,立刻坐直了身子。
瑤台出租屋的一切,不是賣了,就是燒了。他回到河南,陳菊的喪事開始料理,他成日躲在房間不見人。房屋的牆上掛著陳菊放大的頭像。他走到哪,眼睛就跟到哪,晚上,他連廁所都不敢上。
後事料理完,家里人就開始幫他張羅婚事。他騎著摩托車到處相親,相一個,就和大哥商量一個,要麼太老,要麼太醜,要麼帶著孩子,十幾個,大哥都不滿意。有女人問:「你兒子還出來麼,他連親生母親都砍了,能保證他不砍我嗎?」
25「寂寞這種事嘛,你覺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廣州站前路,周周的檔口停著一溜奧迪BMW,大老板們特別愛光顧這家燒烤店。18歲的周周穿著黑色的衣服周旋於各路人馬之間。這個男孩長得很胖,一笑起來就看不到眼睛。他聲音響亮,愛笑愛說話愛做各種手勢逗人發笑。他跟城管混得很熟,城管經過,他熱情地朝他們揮揮手。
最近廣州「創衛」,他也不敢輕易擺出來——城管換了一批新的了。兩年前,他總被媽媽打罵,現在他能獨當一面。
大部分時間,他是快樂的。
他說 :「寂寞這種事嘛,你覺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11月20日深夜,周周的檔口移到後面的街。風很大,他們拿出小爐取暖。張柱良拿起叉具,在爐前用心地烤著一個雞腿。烤好後,他和周周的媽媽聊了幾句,在路邊喝完一瓶啤酒,慢慢朝宿舍走了。
夜很靜,聽得見風呼呼地吹。初冬的月光極好地灑在小街上,樹枝搖擺著腰肢。他的身影就在明與暗之間忽隱忽現,一會兒,就看不見了。
26兒子小的時候
張柱良最後還是回到了廣州。
九月的一個下午,天氣變得微微凉,下著小雨。他去看守所看了張明明。這是事發後父子倆第一次見面。他穿著短褲,T恤,橙色馬甲,顯得有些許胖,皮膚變白了,透著微微紅暈。張柱良大哭失聲:
你如果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知道錯在哪里,就跟別人說,爭取早點出來。
……
張明明只是久久地低著頭,20分鐘一句話也沒說。
張柱良時常感到很恍惚,仿佛自己是在看電影。他想著,「如果我的老婆被人殺了,那我是搭上性命也要報仇。如果我的兒子殺了人,我就算傾盡所有也要幫他減刑。可現在是我的兒子殺了我的老婆。」
想起這些事,他的手總是微微發抖。
他開始同情他了,覺得自己應負的責任越來越大,可有時又想,當年父母對待我們可要差得多。
多年以前,張柱良偶爾賭光了錢,在鐵路的一端坐上悠悠的火車。
而張明明總在鐵路的另一端,河南老家,翹首等待,「爸爸就回來了,他會給我帶來好多好吃的,好玩的。」
兒子更小的時候,張柱良帶著他到處玩。
他小心翼翼地問兒子:「給你生個妹妹好嗎?」
「不好,淘氣。」他又哄著他。
他改口了,「好——把她送到安陽,淘氣。」
(本文所有細節來自當事人回憶、記者調查及相關公開資料,實習記者田原、陳博雷亦有貢獻)
註:
本文採訪時間:2007年6月19日—2007年11月21日
本文主要採訪對象:
張柱良(化名):張明明(化名)父親
劉德亮:張柱良初中同學
張光榮(化名):張柱良大哥
阿強(化名):張明明堂哥
中港皮具城保安老盧
金泉學校辦公室主任
雜貨店老板
電話店老板
張明明好友:周周、佳林、小超
張明明網友:小白(網名)、貪玩的男孩(網名)、少爺(網名)等
因張明明犯案時未成年,警方拒絕了本刊的採訪要求。
單讀君想聽聽你的看法:
當你讀完了林珊珊的作品之後,你想對她說些什麼或問些什麼?我們會在沙龍上以提問的形式轉告給她。
點擊文末「閱讀原文」鏈接,收聽首期「單讀」音頻節目《日瓦戈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