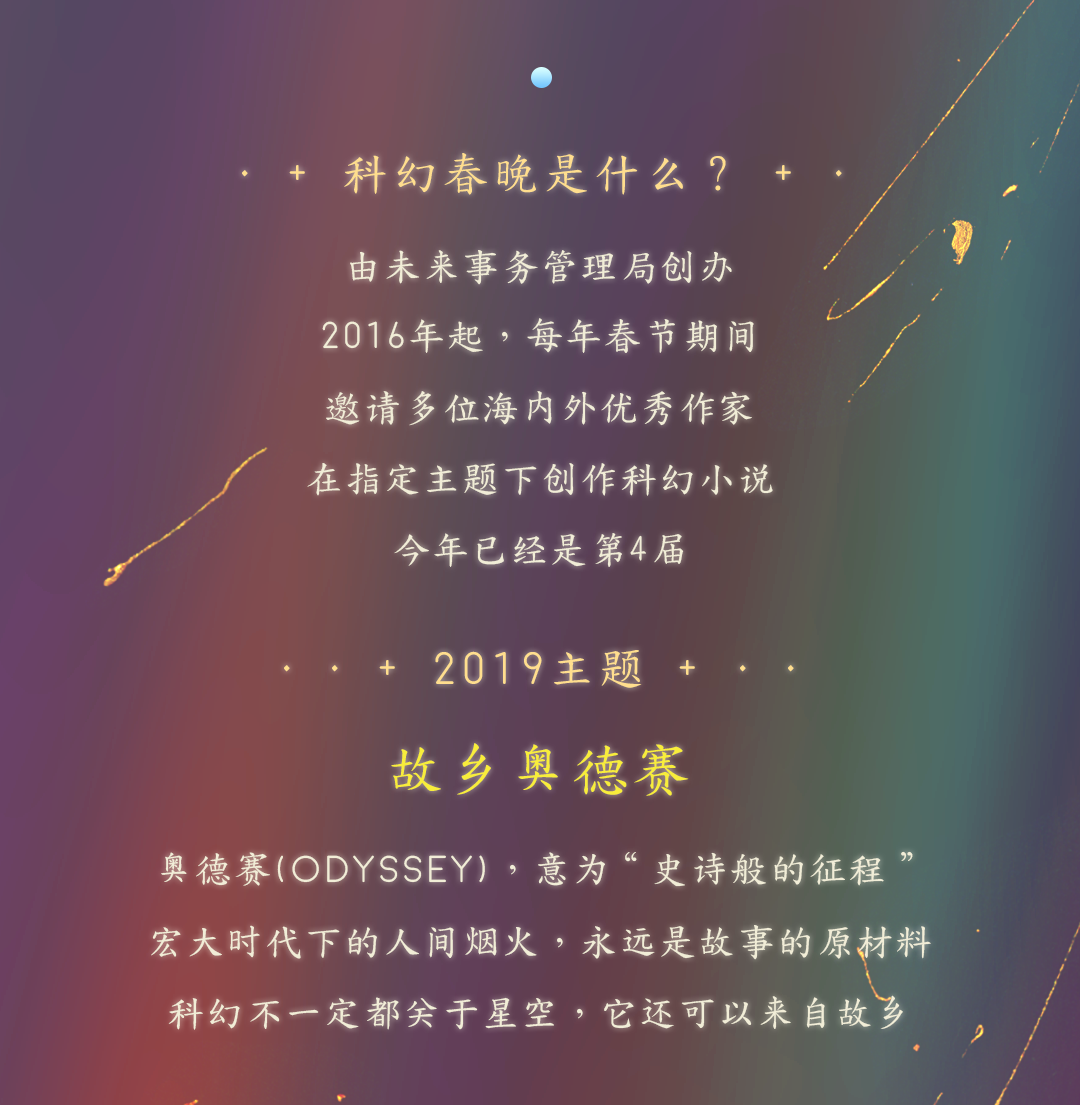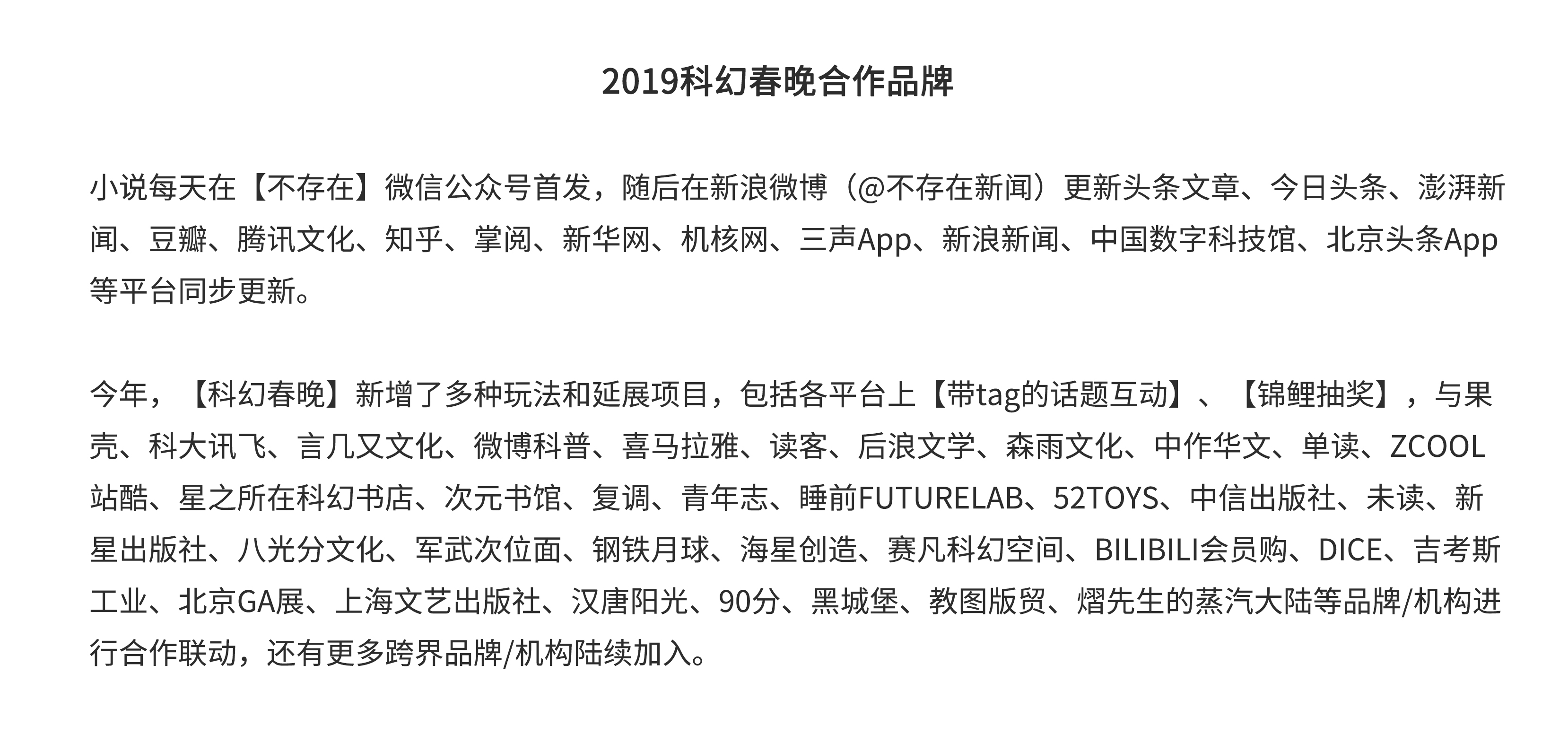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編者按:太陽系邊緣,鑽井工人為了趕在年三十見兒子一面,跳上了回地球的渡船,一場從水行俠星出發,越過天王星、土星、木星和火星,直到中國遼河的公路之旅開始了。假如宇宙里有群人,一年一度,跨越萬水千山,像候鳥一般奔向藍色家園,那一定是中國人。
遼河天涯
滕野 | 科幻作家,地質學專業,代表作品《至高之眼》《第四人稱》 《黑色黎明》 《災星》等。《至高之眼》《第四人稱》分別獲首屆「未來全連接」超短篇科幻小說大賽金獎、銀獎。《時間之梯》入圍第二屆燧石文學獎幻想類最佳中短篇小說。參加過三屆科幻春晚,在第二屆中發表的《宇宙牌香煙》曾被譯為韓文,發表於韓國科幻雜誌《鏡》。
生命中總有那麼一些時刻,你明知它們遲早會到來,卻永遠無法做好準備。比如兒子轉眼就長大成人,比如兒子突然決定遠行,並不再回來。
我試圖說服他不要離開,或者至少等我兩年後回去時再離開。我勸他想想家鄉的天空,想想風、雲、雨、雪和日光,想想他所認識的每一個人,再想想這一生可以做的一切事情。
但我失敗了。過去的許多個夜晚,我一直在問自己怎麼養育出了這麼一個志向遠大的兒子,更要命的是,這小子居然還有做到志向的能耐。
作為對我苦口婆心的勸說的回答,兒子發來了新先驅計劃的啟動通知書,終結了我們之間漫長而徒勞的爭論。
我拋下這份曾讓我夢寐以求的工作,上了我能找到的最快的船。
「我只能送你到朱庇特空間站。」老鼠告訴我,「到那兒之後,會有另一個人帶你回內太陽系。」
我搭乘的河貍號礦船是艘龐然大物,它平時都在水行俠星軌道外的柯伊伯帶深處活動,像真正的嚙齒動物那樣貪婪地啃食小行星,把它們粉碎、消化——準確地說是熔化——並冶煉出各類金屬。
偷渡是一門古老的生意,即便在遠離太陽的深空中,它也能找到讓自己生根發芽的土壤。老鼠的合法身份是私營礦船老板,地下身份則是經營偷渡航班的蛇頭。他帶我穿過河貍號下層的冶煉區,前往我的「客房」——一具老舊的標準冬眠艙。
偷渡者是一種非法貨物,沒有資格要求舒適的環境。按照慣例,這具冬眠艙會被澆鑄在一個巨型金屬錠中央,以躲避海關查驗。
「冬眠艙已經超齡服役,一旦冷凍和絕熱系統出了毛病,你可能會死。」我躺進冬眠艙後,老鼠扶著艙門說。
我點點頭。
「如果你沒死,但海關查出河貍號有問題,我會直接把你和金屬錠拋進深空,你還是要死。」老鼠又說。
我再次點點頭。
「現在,最後一次機會,你可以離開河貍號,或是堅持回家。當然,無論如何,你付過的錢不會退還。」
我咽了口唾沫:「我要回家。」
「很好。如果你路上醒了,那多半是液氦循環有問題,擰擰就行。」老鼠指指冬眠艙里的一個閥門,「祝你一路順風,先生。」他關上了艙蓋。
我在黑暗中默默等待。制冷機開始運行,液氦流動的低鳴聲響起,松垮垮的制冷管道在我頭頂跳個不停,如果它不幸泄露,我幾秒鐘之內就會成為一具晶瑩剔透的冰雕。八年前來到水行俠星時,我也躺在一個這樣的冬眠艙中,光在路上就花去了整整一年。但那一年我都在沉睡,從主觀感受上說,我只不過做了個短短的夢,醒來就到了天涯。
天涯空間站是人類世界的盡頭。從這里俯瞰,水行俠星的大氣層猶如一片深邃的海洋,上面散布著星星點點的燈光——每一點燈光都是一口油井,它們像銀色的沙丁魚群一樣,隨著水行俠星上的風暴迅速移動。
這里是太陽系最大的油田。
石油行業聽起來陳舊而落伍,與這個銳意進取的時代格格不入。像每一個敏感的父親那樣,我很在意兒子對我的工作的看法。離開地球前,我鼓起勇氣問了兒子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卻令我十分意外:「爸爸,您很像先驅,像我最想成為的那種人。」
這是個很高的評價,我為此開心了很久。
先驅是一批偉大的開拓者,他們的時代被稱為先驅世紀。在那充滿光榮與夢想的一百年里,先驅們向深空狂飆突進,足跡遠達水行俠星。他們留下了許多遺產,天涯空間站就是其中之一。
從某種意義上說,天涯站與我的故鄉很相似。我的父輩不曾深入星空,但在我看來,他們跟先驅一樣偉大。過去曾有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那時為了開采石油,父輩們令一整座城市從遼河口荒涼的蘆葦蕩里拔地而起。
天涯站也是個石油城市,除了漂浮在水行俠星軌道上這一點以外,它和那座東北小城並無不同。剛到這里時,我發現自己像多年前的父輩們一樣,面對著一片遼闊、遙遠到難以想像的新天地。
自先驅世紀以來,各大空間殖民地的計時方法都以地球為基準,以照亮地球上國際日界變更線的那縷曙光抵達殖民地的時刻算作一天起點。於是太陽系內也出現了不同的時區,火星時區比地球慢14分鐘,木星時區比地球慢40分鐘,最遠的水行俠星時區則比地球慢4個小時。
與人類天文台規定的時差不同,這是由最基本的自然法則之一——光速規定的時間延遲。起初,我偶爾還會想想地球上的父親和兒子此刻在做什麼,但後來我發現,在深空中談論「此刻」沒有意義。關於地球的一切信息永遠來自四個小時之前,有句話說得好,光錐之內就是命運,地球上的「此刻」在我的命運之外。
這大概是人間最遙遠的距離了。
我事先算了算,要趕得及再見兒子一面,必須在這個冬天結束前上路——我說的是地球上的冬天。水行俠星沒有氣候變化,這顆乏味的巨行星永遠被寒冷和黑暗籠罩,但地球此刻剛剛完成了一次四季輪回,按古老的歷法計算,又快過年了。
當初送我來的那艘飛船叫波塞冬號,它受雇於經營天涯油田的尼普頓公司,長年往返於水行俠星與地球之間。但我跟尼普頓公司簽了十年的合同,從法律上講,我兩年後才可以坐波塞冬號回家,所以我必須想別的辦法。
四小時前,我離開了天涯站,前往我負責維護的天涯油田68號井。
水行俠星寧靜的外表只是偽裝,它的大氣層中充斥著氫氦氣流構成的風暴。無論經歷過多少次,墜入水行俠星的過程永遠像第一次那樣驚心動魄,潔白的維修船以自由落體的方式從天涯站掉下,就像一顆冰晶從星空落進寒冷的北冰洋。
你見過的最深、最美的藍色是什麼樣子?天空?海水?矢車菊的花瓣?藍閃蝶的翅膀?不,和水行俠星的大氣層比起來,它們都黯然失色。在漫長的自由落體運動過程中,風暴的蔚藍色調不斷加深,那顏色起初很淡,隨後便迅速變得黏稠、凝重,像畫家使用的油畫顏料,維修船則仿佛油畫幹透前不幸落在畫布上的飛蟲,無論如何掙扎,都只能被這藍顏料的泥沼永遠吞沒。
68號井是個巨型平台,集成了眾多開采、提煉、加工和運輸設備。依我看來,「井」這個字眼實在太委屈它了,它就是一座漂浮於風暴中的金屬島嶼。每當舷窗外的藍色深淵中亮起刺眼的探照燈,我就知道68號井到了。
從童年起我便熟悉這種光芒。在東北的寒夜里,它比月亮更讓人安心。當你在晚歸途中穿過田間小徑,兩邊只有黑漆漆的曠野,不湊巧又碰上了壞天氣,唯一能指引道路的就只剩下那些被探照燈照耀著的高大井塔。它們像豎立在地平線上的路標,風雪越大,它們越明亮,就算認不出方向,只要朝著它們走,便一定能找到房屋、暖氣、電話、裝滿開水的老式熱水瓶,以及為你指路的人。
過去八年里,我無數次沿著這樣的燈光飛往68號井。但我今天不會去檢修它。以後再也不會了。
68號井下方掛著許多垂入水行俠星大氣深處的甲烷采集管,其長度從數百至數千千米不等,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盡頭,最長的一根放在地球上能把烏魯木齊和上海連起來。我們繼承了地球上石油工業的習慣,稱它們為「鑽桿」。我駕船從平台下的鋼鐵森林間穿過,千百條鑽桿在我周圍有節奏地緩慢起伏,就像地球上古老的抽油機——我家鄉的人們管它們叫「磕頭機」。抽油機都是毫無美感的鐵坨子,不合時宜地矗立在綠油油的草地、樹林、稻田和蘆葦蕩里,強行把一切自然風光都打上人類工業深刻而醜陋的印記。它們笨重的前端上下做著往復運動,永無休止,像用額頭反復撞擊地面的巨人。我小時候站在原野上一眼望去,常常覺得自己像個皇帝,從眼前到天邊跪滿了不停磕頭的抽油機,那場面滑稽中還帶著一種古怪的莊重感。
但據我父親不久前告訴我的消息,隨著天涯油田蓬勃發展,水行俠星已經能供應太陽系內所有人類居住地的石油需求,地球上的石油行業正在死亡,最後一口油井即將關閉,他也將隨之退休。
某種角度上講,是我的工作淘汰了我父親的工作。這令我心情多少有些複雜。
離開68號井後,我又飛了很遠的一段路程,終於隱約看到河貍號龐大的身軀。老鼠定期將礦船停泊在水行俠星大氣層內,以風暴為掩護,接偷渡客上船——這樣的營生他已經幹了許多年。
我花了一大筆錢才買到躺進這老舊、狹窄的冬眠艙的資格。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我摸索著摁亮艙內照明燈,從懷里掏出一張仔細折好的地圖。這是我隨身攜帶的唯一行李,老鼠從不允許偷渡客大包小裹地上船。
水行俠星到地球的距離將近四十五億公里,這個天文數字遠遠超出人的直觀認知能力,因此我只能用這種辦法大概可能自己離家還有多遠:把太陽放在天安門廣場上,將各大行星的軌道半徑按比例縮小,那麼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都在北京和石家莊之間,木星在鄭州,土星在長沙,天王星在南海中央,水行俠星則在印度尼西亞。
我從衣袋里找到一根短短的鉛筆,在赤道上的群島下方畫了個圈——這就是我的出發點。
我頭頂液氦管道跳動的頻率加快了,隨著冬眠系統啟動,久違的困倦感從腳底漸漸升起,它如有實質,像液體一樣漫過我的膝蓋、腰際和胸口。睡眠很快就淹沒了我。
我下一次醒來時,液氦管道的嗡鳴聲停止了,四下里一片漆黑,靜得可怕。我打開照明燈,在身邊那個控制面板上按了幾下,一個不耐煩的聲音響起:「什麼事兒?不是告訴你醒了就擰擰閥門嗎?」
「老鼠?」我認出了這個聲音,「我們現在到哪兒了?」
「剛過土星軌道,離木星還遠著呢。我警告你,你摁的是緊急聯絡鈕,除非你要死了,否則別動這玩意兒。如果過行星海關的時候讓海關檢測到金屬錠里有異常,我就把你直接扔進太空。」
土星。土星。我摸索著抽出懷里的筆和地圖,就著黯淡的燈光,找到長沙的位置,畫上一個圓圈。
我已經越過浩瀚無邊的南海,踏上陸地。從這里開始,可以稱為「故土」了。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但我猜離河貍號出發已經過去了幾個月,地球上的春天應該即將接近尾聲,漫長的夏季很快就要到來。
還真是有趣。自先驅世紀以後,車馬和書信再次變得緩慢、遙遠,我們要花幾個月從一顆行星飛往另一顆行星,就像古代跋山涉水的旅行者一樣。河貍號的速度約為每小時五萬四千公里,接近太陽系的第三宇宙速度,但相對於無盡的深空,它就像孩子們放入溪水的小小紙船,慢悠悠地在星風中順流而下,飄向太陽。
我用力轉了幾圈液氦閥門,制冷管道重新跳動起來,艙內氣溫又開始下降。即將沉入睡眠的海洋之際,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了一句詩,雖然它和長沙沒有什麼關係:
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這樣醒了又睡的過程在航行中反復了好幾次。最後一次醒來時,我聽見了類似鏈鋸切割金屬的刺耳聲響,與此同時,一陣劇烈的震動從四面八方傳來。刺耳的聲音越來越大,它從我頭上徑直經過,聽起來好像包裹著冬眠艙的金屬錠正被分割成許多小塊。我默默祈禱那切割工具——無論是鏈鋸、刀片還是別的什麼東西,千萬別直接把冬眠艙鋸成兩截。
切割聲持續了很久。當它終於停止,冬眠艙蓋也隨之滑開,突如其來的燈光刺得我一時睜不開眼:「好,你還活著,那就快滾出來。」老鼠抓著我的衣領,把我從冬眠艙里直接拖了出來。
我跌跌撞撞地站起身,周圍看起來像是個巨大的倉庫,藍色的燈光從高空照射下來,讓這里顯得格外寒冷,而事實上這里也的確很冷。
「這是哪兒?」我打著哆嗦問。
「歡迎來到朱庇特空間站。」老鼠拍拍手,「從這兒起,咱們倆該分道揚鑣了。」
朱庇特空間站是一座懸浮於木星大紅斑上空的城市,也是外太陽系最大的空間殖民地,但我從未來過這里。
離開老鼠的倉庫後,我穿過朱庇特空間站的中央通道,這里人潮洶湧,基本都是來度假的遊客。在太陽系邊緣生活了八年,我幾乎忘記了世界上原來有這麼多人。朱庇特站就像地球上的熱帶海島,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就是世界盡頭了;水行俠星的天涯站更像南極,人們都知道它遙遠,卻根本不清楚它究竟有多遠。在中央通道兩側巨大的舷窗外,木星著名的大紅斑緩緩旋轉著,像一只巨眼,冷漠地旁觀著熱鬧的人類社會。
根據老鼠的指點,我在一家吵鬧的酒館里找到了一個乾癟、黑瘦的中年男子——貍貓。老鼠說他有辦法讓我從木星偷渡回內太陽系。理所當然,我又掏了一大筆錢。
幸好,貍貓不打算把我澆鑄進金屬錠里。按他的說法,他們會把偷渡客和冬眠艙運往木衛一,在那里,冬眠艙會被封入一顆直徑數十米的隕石內部,然後他們的船將推動這顆隕石穿越小行星帶。
如果攤開星圖,你會發現太陽系里還有一個小星系,這就是木星和它的近百顆衛星構成的「雲」。從伽利略時代至先驅世紀的一千多年里,木星的衛星數量不斷被刷新,直至朱庇特空間站建成、天文學家近距離清點過一遍後,「木星系」的成員才完全確定下來。這些衛星大小不一、公轉方向不同,甚至軌道都不在一個平面上,如此混亂的天體結構為偷渡者提供了絕好的掩護。木衛一軌道上漂浮著一顆直徑大約五十米的隕石,隕石內部被挖空,數十個和我一樣的偷渡者就躲在這里面,一艘小功率貨船會慢慢推動隕石離開木星引力井,帶我們徑直渡過內太陽系的護城河——火星與木星間的小行星帶。
按理來說,小行星帶內天體過於密集,為了安全,一般的飛船——當然是合法的那些——應該從黃道面底下繞過小行星帶,這條航線被稱為「鯨落航線」。
我看過一些鯨落航線的照片。離開火星後,深空飛船紛紛調頭向下,在太陽微茫的輝光中,它們的色澤猶如骸骨一般蒼白、明亮,仿佛一群墜入海底的巨鯨。五十萬顆小行星匯成的大河就從鯨落航線上方流過,晝夜不息。
但我們必須徑直橫穿這條大河。想想被封在鋼錠里的那些日子,這趟旅途好像也沒那麼難以忍受了。出發之前,我在那張地圖上鄭州的位置畫了個圓圈。
歸鄉之路,已至中原。
貍貓用的冬眠艙質量似乎比老鼠的好得多。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到了旅程的終點。
爬出冬眠艙後,我看了看周圍,這里似乎是一間地窖,天花板上有一盞昏暗的電燈,濕漉漉的牆壁和地面上長滿了青苔。
貍貓的面孔忽然從黑暗中浮現:「醒了?那就出去。」他指指地窖一角的樓梯。
我跌跌撞撞爬上樓梯,打開一道活板門,外面黑漆漆一片,但我聽到了風聲和樹枝抖動的沙沙聲——不是中央空調,也不是溫室里的水培植物,是自然形成的大氣流動和生長在泥土中的樹木之間的碰撞。
我渾身打了個激靈。寒冷,徹骨的寒冷。對習慣了恒溫空間站的人來說,這種感覺實在有些陌生。我抬頭往上望去,在樹影的縫隙中,我看到了星星。
我認出了那些熟悉的形狀。獵戶座,大熊座,北斗,北極星。
我蹲下來抓了一把泥土,湊到鼻子底下用力嗅了嗅,隨後劇烈咳嗽起來。肺部的疼痛感告訴我,這不是夢。
「這兒離北京不遠。」貍貓說,「恭喜你,平安到家。」
家?每次從冬眠中醒來後我的腦子都不大靈光。我甩了甩頭,終於記起那座小城和北京的相對方位:「我家不在這兒,還要往北走,過山海關。」
「那就不幹我的事了。」貍貓的眼睛像真正的貓科動物一樣在黑夜中閃閃發光,「不過呢,我看你沒準備冬天的衣服吧?在水行俠星呆久了,忘了地球上有四季之分?」
我愣了一下。我確實沒考慮到這一點。「算我好人做到底,我可以帶你去最近的鎮子。」貍貓狡黠地說。
我望望遠處,陌生的森林,陌生的大山,陌生的道路。我別無選擇,只能掏出錢包,乖乖讓貍貓再宰上一刀。
「我喜歡你們中國人。」坐著車子往山下開去時,貍貓慢悠悠地說,「過鯨落航線回內太陽系的船里,有一半乘客都是中國人。你們很戀家,就像候鳥一樣,年年歸巢。」
「老傳統。」我說。
「我不理解這種傳統,但我喜歡它,它讓我的生意永遠顧客盈門。」貍貓隨著車子的顛簸搖頭晃腦,「可是說真的,就算從水行俠星那麼遠的地方趕回來……你們怎麼說來著?‘過年’?你也只能過上下一個年,這種習俗還有保留的必要嗎?」
我這才想起,距離我從天涯站出發,已經又過了一輪春秋,眼下的冬天和我出發時的那個冬天並非同一個冬天。但在我自己看來,這條漫長的旅途只不過是睡了幾覺罷了。
「今天是幾月幾號?」我問。
貍貓在車載控制台上摁了幾下,日曆界面跳了出來,我念了兩遍年份,不是錯覺,的確過去了一年。「這個日期能不能換算成農歷?」我又問。
貍貓又摁了兩下,日曆上的數字變成了漢字:臘月廿七。
我算了算時間,兒子離去的時刻已經越來越近,我應該勉強趕得及送他一程——按他告訴我的說法,他們將要前往比鄰星,開創第二個偉大的先驅世紀。他很優秀,也很幸運,成為了首批遠航的水手之一。
只送意識。他們是這麼說的。我想,那一定是很了不起的技術,拋棄肉體這個無用的累贅,把人用電磁波的形式通過深空網路、大功率天線和射電望遠鏡送出去,他們會化作一道明亮的光芒,劃破星空——換句話說,他們將化作光錐,與自己的命運融為一體。
帶我到小鎮後,貍貓消失在了夜色中,我餘生再也沒有見過他。
我仍然是個偷渡客,按官方記錄,我這會兒應該還在天涯空間站里,因此我沒法大搖大擺地買一張車票回家。從每年的偷渡客數量來看,肯定有什麼辦法能把身份記錄從水行俠星搞回地球,不過我眼下顧不上操心這事兒。我先買了套棉衣,接著找一家旅館狠狠睡了一覺。第二天醒來後,我在鎮子上雇了一輛車子。當然,年關將近,又是跨省長途,少不了還得再掏一筆錢,但跟之前花出去的相比,這簡直就是毛毛雨了。
車子行駛在晴朗的天空下時,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雖然一開窗就冷風撲面,但隔著玻璃,陽光照在臉上的溫度十分怡人。
司機是位頭髮已經有些灰白的老人,十分健談。聽說我曾在水行俠星工作,他好奇地瞪大了眼:「你們在那兒幹什麼?」
「開采石油。」我說。
「我還以為石油早就沒用了呢。」老人搖搖頭,「聽跑長途的老兄弟們跟我講,山東和東北的油田荒廢了得有幾十年了。」
「石油有用,一直有用。」我笑道。
一百年前石油是工業的血液,一百年後依舊如此。曾有些人認為再來一兩次能源革命,我們就能擺脫對石油的依賴——但歷史慣性的強大超乎想像。即便人類已經進入深空,石油依舊不可或缺。藥品、染料、織物、化學制劑、機器零件、飛船外殼、空間站構件……沿著每一樣現代產品的製造流程向上追溯,在源頭處幾乎都能看見石油的身影。
「可我不懂啊,石油不是古代的那些個動物、植物死了之後,屍體變的嗎?」老師傅拍拍方向盤,「水行俠星上也有這東西?」
「我們只是借用了地球上的習慣叫法而已,實際上我們開采的是甲烷。」我耐心地解釋。
「甲烷?」老師傅沒聽懂這個詞兒。
「就是沼氣。」我補充道。
「大糞池子里發酵出來的那玩意?」老人看起來一下子失去了興趣。
我樂出了聲。老人說得也沒錯,但水行俠星上的甲烷可不是發酵出來的。
在地球上的光明和溫暖中長大的人很難想像太陽系邊緣的寒冷。極端低溫下,水行俠星大氣中的甲烷凝結成了固態冰晶雲,它們濾掉了太陽光譜中的紅光成分,只讓藍光通過,這也就是水行俠星呈藍色的原因。
如今,甲烷是工業的造血細胞。石油的主要成分是碳和氫,通過裂解、加成、縮聚、閉環等多種反應,甲烷能生成複雜的碳氫化合物,即傳統意義上的各種石油產品。地球上不採用這套辦法的原因純粹是成本太高,並非技術上有什麼無法逾越的壁壘。可在天涯油田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水行俠星上甲烷質量的總和等於十七個月球,用之不竭,以甲烷合成石油產品的成本低到了驚人的地步。
「哎,年輕人,」隔了一會兒,老師傅又挑起了話頭,「我聽說啊,水行俠星上有山那麼大的鑽石,是不是真的?」
「應該是,但沒人親眼見過。」我說。
「要真有,怎麼還能沒人見過呢?」老師傅露出失望的神情。
「因為誰都不敢去找。」我回答。
根據天體物理學家的計算,水行俠星大氣層之下有一片液碳海洋,里面布滿了巨大的碳質島嶼——從化學成分上講,碳就是鑽石,所以你也可以採用更浪漫的說法:在水行俠星永恒的風暴下面,有一片鑽石之海,海上漂浮著無數鑽石冰山。
沒人確切知道鑽石海是什麼樣子。氣體巨行星內部的高溫高壓足以毀滅任何探險飛船。但在藝術家們的想像中,那里是一個暗藍色的古老夢境,鑽石冰山隱匿在幢幢陰影中,海面黑漆漆一片,波濤沉重而黏稠;當天空中的雲層偶爾散開,一縷光線輕輕碰撞鑽石冰山的頂峰,奇跡立即發生,就像上帝的手指觸及亞當,燦爛的華彩從冰山頂端那一點綻放、爆炸開來,令這個沉睡的夢境短暫地蘇醒,變得像童話一樣蔚藍。
老人指指窗外的天空,問了我最後一個問題:「水行俠星的顏色,是什麼樣兒?跟地球比起來呢?」
我恍惚了一下。
作為在石油城市長大的人,天涯站的一切都令我回憶起故鄉,剛到那里時我還覺得很欣慰,能在世界盡頭看到些熟悉的事物;但後來,這種回憶變得越來越煩人,它像螞蟻一樣,總是在夜深人靜之時嚙咬我的心臟和夢境,而且每一夜都咬得比前一夜更疼。
最他媽要命的是,水行俠星是藍色的,讓人每看一眼就想起地球上的天空,想起家鄉的風、雲、雨、雪和日光。
「一開始,我覺得水行俠星的藍色和地球很相似,但時間長了,就能看出它們一點都不像。」我終於說,「水行俠星的藍色很暗,很冷,像爐子里滅了火的灰燼那麼暗,像冬天遼河上砸出的冰窟窿那麼冷。」
老人哦了一聲,這一聲拖得很長很長。
到山海關後,老師傅停下了車子,任憑我怎麼加價都不肯再往前開一公里,只說他也急著回家過年。
於是,臘月廿八的下午,我站在山海關古老的城牆下,茫然四顧。我滿頭大汗地四處打聽、詢問,但還有兩天就是除夕,根本沒人肯接我的活兒。
這是個奇怪的時代,隨著文明的疆域向深空推進,古老的傳統卻愈發頑固。我想起先驅世紀的一則傳聞:每到十一月,火星基地里的中國人就會集體請假回地球,理由是給回家過年打提前量,以當時的飛船速度,他們到家剛好可以趕上年根兒。各大行星都建立了殖民地後,這個傳統被中國人撒向整個太陽系,一年到頭深空里都有載著回家過年的中國人的飛船在飄。
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也許春運是永恒的吧。
人逼急了什麼轍兒都想得出來。夕陽西下時,我從山海關的照相館買了匹馬。對,就是在歷史遺跡前面拴一匹馬給你拍照的那種店鋪,這個行當至今仍然沒有消失。
我從水行俠星出發,越過了天王星、土星、木星和火星,回家的最後一段路竟要靠騎馬。
在照相館老板指導下,我花兩個小時學會了怎麼待在馬背上不摔下來,可我沒時間去練習更進一步的技巧了。臘月廿九的早上,我出發了。除了必要的睡眠、進食和休息時間外,我馬不停蹄地沿著大路向東北方前進——字面意義上的馬不停蹄,我胯下這匹胖馬頭幾個小時一直氣喘籲籲,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反而慢慢精神了起來,步子也開始變得穩健,我猜或許是祖先的基因正在它體內蘇醒。
可能人身上也有某個基因片段控制著「回家」的欲望吧。它就像定好了時的生物鐘,平日里沉睡不醒,年關一近便開始不停響鈴,驅使無數人們從無數遠方踏上相同的歸途。
出了山海關往北,遍地大雪,走一步冷一截。馬兒噴著厚重的鼻息,馱著我穿過白茫茫的群山和曠野。
這條道路上或許已有數百年不曾響起馬蹄聲。東北大地如同一幅惜墨如金的國畫,天空是留白,大地也是留白,除此之外只有一人一馬兩個渺小的影子,就像老天爺拿著墨筆在雪地上隨意蘸了兩點。我像古老歲月里的牧民一樣,只身打馬穿過關外的草原。
臘月三十傍晚,我終於看見了蘆葦蕩。
這是這顆星球上最大的蘆葦蕩,往四個方向都連到天邊,在夕陽的光線下,葦子上厚厚積雪被映得像炭火一樣。穿過葦蕩的時候,偶爾還能看見葦子下有麻雀在蹦跳,它們啄著被薄冰覆蓋的黑泥土,翻找草籽。如果這里被埋入渤海灣,千萬年後,這些蘆葦都會變成新的石油。蘆葦蕩深處矗立著幾個龐大的陰影,那是早已廢棄的抽油機,它們銹跡斑斑的外殼黯淡而醜陋,與潔白的雪地和枯黃的蘆葦格格不入。天涯油田建成後,它們就被時代淘汰,抽油機的前端向天空高高揚起,定格在了停止運轉的一剎那。這些鋼鐵巨人終於不再叩頭,落日餘暉中,它們的輪廓顯得莊嚴無比。
不知為何,看著那些廢棄的抽油機,我想起了水行俠星上的68號井。它像遨遊於深海中的一只水母,伸出無數觸須,從水行俠星大氣層中貪婪地汲取甲烷。尼普頓公司甚至希望有一天能造出直達鑽石海面的鑽桿,用水行俠星海洋中的碳和風暴中的氫直接合成碳氫化合物。如果這種技術真的做到,那在人類眼里,整個水行俠星將變成一滴懸浮在宇宙中、圍繞太陽旋轉不休的石油。
我腦子里冒出了一個不著邊際的念頭。水行俠星被天涯油田榨乾後會是什麼樣子?天涯油田被人類廢棄、那些油井停止生產後又會是什麼樣子?它們或許會像披頭散發的幽靈一樣,在藍色深淵中漫無目的地流浪,直到某一天被風暴卷入深不見底的鑽石之海。但水行俠星沒有氧氣,因此它們永遠不會像地球上這些工業遺跡一樣生銹、腐朽,千年萬年之後,它們依舊可以光潔如新。
夕陽的光線逐漸熄滅,我猛然發覺自己正面臨著一個古老的難題,過去千百年間,它曾阻撓了無數急於趕路的旅人:黑夜。
每當夜幕降臨,人類走過的道路上,必然會有燈光自動亮起。自電燈發明以來,這似乎已經成了一條新的自然法則。可在這寒冷的曠野里,我舉目四望,茫茫黑暗中只有北風吹動葦桿的聲音,一陣熟悉而陌生的恐懼感湧上心頭——我從沒想過人在這個時代還會迷路。
我本能地抬頭尋找月亮,但是天上只有黯淡而稀疏的群星。我徒勞地在群星中搜尋了半天,才想起那句年代久遠的諺語:三十晚上無月亮。
我在蘆葦蕩里漫無目的地亂走了很久,終於看到遠方亮起一束直入雲霄的淡白色光芒。那是我童年時最熟悉的光芒——油田井塔上的探照燈。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樣朝那里奔去。沒錯,燈光中矗立著一座井塔,塔下的空地上有一排老式活動鋼板房,鋼板房的窗戶上糊滿了水汽,顯然屋里有人在烤暖氣或燒爐子。
我敲響了鋼板房的門。片刻之後,門開了,我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龐,熟悉到我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
門里的父親也愣愣地看著我,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回來了就好。」父親用搪瓷杯子給我倒了滿滿一杯開水,「先暖暖身子。」
「爸,你沒在家待著?」我問。
「這口井明天就關了。」父親指指窗外,隔著厚厚一層水汽,井塔上照下來的燈光顯得朦朧而耀眼,「我想再看看它。」
「油田最後一口井?」我說。
「地球上最後一口井。」父親平靜地回答,「沒什麼,也該關了,跟水行俠星那樣的大油田比起來,地球上這點兒產量早就不夠看了。」
我點點頭,一時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老嘍,沒用嘍。」父親忽然敲敲自己的膝蓋,感慨道,「工人老了,油田也老了。我還以為會有很多人來看看這最後一口井,好歹也算見證一下歷史……」
我依然不知該說什麼,只好端起杯子不停喝水。地球上這個古老的行業終於走到了盡頭,今夜,在歷史的一角,一根由石油鑄就、明亮了數百年的蠟燭默默燃盡了。
「對了,你兒子走了。」父親像忽然想起來了似的,補充道。
我喝水的動作停了一下。「什麼時候的事兒?」我問。
「就三四個小時之前吧,新聞上剛播了。」父親看起來很平靜,「第一批遠征比鄰星的先驅,連他在內一共十五個人。和他們說的一樣,只送意識。」
只送意識。這四個字像烙鐵一樣燙在了我的腦海里。
三四個小時之前。那麼,我兒子此刻應該剛剛抵達水行俠星附近。
我想提醒自己,在深空中談論「此刻」沒有意義。光錐之外,與命運無關。但我發現自己似乎沒法清晰地思考。
「你放心,他的身體國家會送回來,像英雄那樣送回來。」父親又補充道。
我把臉埋進了胳膊。父親的聲音從比水行俠星還要遙遠的地方傳來。「你這麼想,今晚他在地球上,我在地球上,你也在地球上,咱們一家好歹還是過了個年,挺好的。」
窗外,更加遙遠的地方似乎響起了鞭炮聲。
(責編:東方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