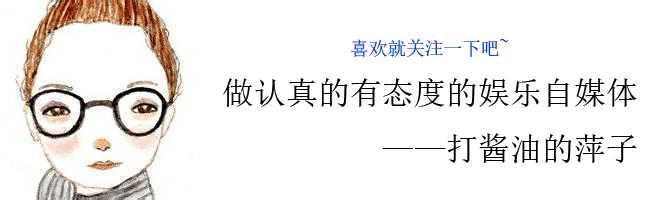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兩年前,播出12年的《康熙來了》停播,令無數康熙粉淚奔不已。
兩年後,作為康熙的兩位王炸組合,蔡康永和小S終於攜手回歸,新節目《真相吧!花花萬物》於日前正式開播。

這檔網綜由《康熙來了》原班人馬打造,雖然名字不同了,但很多人表示依舊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小S早在預告片里就說過:「我們在一起就是《康熙來了》,因為他就是蔡康永,我是徐熙娣。」連蔡康永自己都說,既然是我和她,那就不可能沒有《康熙來了》的味道。

首期節目邀請了謝娜擔任嘉賓。但第一期播出後,網友評價褒貶不一,大多網友認為該節目在很多方面都不盡人意,用力過猛,還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豆瓣評分也僅有3.6分。

要知道《康熙來了》在豆瓣上的評分可是9.2分。

兩兩對比,難免令人唏噓不已。
蔡康永的溫文爾雅、學識淵博令人印象深刻。蔡康永年輕時曾留學UCLA,並且在1990年獲得UCLA電影電視研究所編導製作碩士學位,其出的幾本書上或多或少的提到了他的這段留學的經歷。
蔡康永在《LA流浪記》中詳細記述了自己在UCLA的經歷。下文的部分內容摘自1998年《痛快日記》,文章內容更實在更明白地說明了他為何求學以及感受,希望對正在申請的大家有幫助。
01

每次翻書,看到寫書的人自我介紹的部分,心里就忍不住納悶——「這些家夥,除了從一個大學畢了業、再從一個研究所畢了業、再進了另一個大學去教書之外,他們這輩子就什麼好玩的事都沒發生過嗎?」

蔡康永年輕時和母親
對很多愛寫書的學者來說,事實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他們的人生,除了分別用A大學、B大學、C大學來當坐標之外,的確沒有更理想的標點符號了。
然而,不可否認的,這些人會這麼心甘情願、而且理直氣壯、而且與有榮焉的,勇敢把以大學為坐標的人生地圖,公布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為——這麼幾所大學的名字,總能夠代表些什麼吧,總能夠證明些什麼吧!
是啊!大學的名字,到底能夠代表些什麼?到底能夠證明些什麼?
02
這樣的問題,一旦被提出來,就好像是當著氣象播報員的面,問他那張看起來很了不起、實際上模模糊糊的衛星雲圖,到底是在搞什麼鬼一樣。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國一所叫「哈佛」的大學的博士。我這好友,在愛情上過得不順利,大家就總會努力幫他找些可能的對象。
可是每次到了要安排見面時候,他就會很乾脆的回絕:「噯呀,人家不會對我有興趣的啦!」
這時就必定有人會加油打氣:「沒興趣?!是哈佛的博士耶!怎麼可能沒興趣?!」
我這好友也就必定會回答:「哼!博士又怎麼樣?!哈佛又怎麼樣?!」
是啊。氣象播報員,自己開口了,「哈佛又怎麼樣?」
03
我自己從一進大學開始,就覺得——「這個地方不對勁」!(蔡康永本科就讀於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
當然並不是說有鬼。有鬼沒什麼不對勁,很多大學都有鬼。
不對勁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學生,還有大部分老師,表面上都煞有介事,骨子里都恍恍惚惚,不知道大學到底是個幹什麼的地方。

我的同學,多半表現的態度是:大學,是人生第一次沒有人盯在後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師,多半表現的態度是:大學,是老師唯一不用盯在後面管的地方。
這並沒有什麼不好。事實上,大學的消極功能,本來就有一大重點是培養互相尊重的原則: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學科與學科之間互相尊重。
不過,我會感到不對勁,是因為這種「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結局」了,接下來,沒有了。
大家不管大家,就是這樣了,你被當掉也沒人管,你不好好教書也沒人管。
連人格展示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說人格的養成了。你有機會展示的,是打撞球的技術、投資股票的靈敏、避孕的花招、擺地攤的口才。這些東西。
偏偏我認為,大學的一項重要的目標,應該是養成人格,而不只是「養人」而已。
於是在這樣的大學氣氛里,我當然是關起大門過我的日子。所幸我念的大學,校園超級美麗,起碼比美國好幾家名校都美,讓我能夠以開闊的環境,做為自閉的居所。

台灣當時的其它大學,也都不會比我念的學校高明多少。排名最前面的那幾所,情況也許好一些,可是根據我這些年來,跟這些大學往來的經驗,充其量也只能覺得,閃耀光芒的,通常只是精彩有魅力的個人,很少是一校在制度上展現的風華、在治學上展現的氣派。
台灣幾十年來,政治大環境上,尚且關關卡卡、踉踉蹌蹌,在這種條件下,要求各大學卓然自成真理與知識之天堂,當然是奢求。
回想政治戒嚴時期,似乎大學里還有機會讓知識人略展不同標準的「風骨」,不像解嚴以後,大學變成資本化社會的育幼院,教室里,老師的行動電話與學生的呼叫器齊響;教室外,老師與學生成為同一家直銷公司的上下線。這一方面有開發中國家的生猛,叫人為之失笑;另一方面,又令人無比惋惜,眼睜睜看見人生最珍貴的事物、與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就為了先賺到手那些錢,以致兩相錯過。
04
就是因為在台灣的大學,見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局面,所以我挑選研究所階段的美國大學時,就特別注意這些學校從招生階段開始,是否就已展現了不同的理念和風範。

從大學階段的英文系念完以後,我就知道文學不可以再往下念,再念勢必會傷害我對文學海闊天空的信賴。
因為已經確認:寫東西必須靠自己,對這條路就暫且放下心來。當時左思右想,覺得電影這池二十世界的大渾水,是非要去沾惹一番才行的。寫字畢竟已經會寫,電影卻完全不會拍,不趁此時練就武藝,更待何時?!
下手一查美國各研究所概況,立刻發現老牌名校幾乎全部不設研究所階段的電影課程,原因無他,一言蔽之——他們覺得拍電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學問。
就拿常春藤諸大盟校來說,當中就只有哥倫比亞大學一家,心不甘情不願的設了一門「導演學與編劇學」的專業碩士學位,算是過濾掉拍電影過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術部分,當然,也同時節省了驚人的硬件器材費用。我還記得那時坐鎮該研究所的,正是以《飛越杜鵑窩》和《阿瑪迪斯》威鎮影壇的大導演米洛斯福曼。
其實不要說是雄霸美國東北角的這些老名校,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級的大校如普林斯敦、柏克萊、西北、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等等,也都最多只肯設立電影理論的相關研究所,沒興趣把拍電影的學問,開成專門的研究所。
除了器材經費是一大顧慮之外,擺在第一位的,當然還是各校自我要求的學術標準。
我是深愛電影之人,也確知電影已累積不少值得保存的文明精粹,對於這些名校的老大心態、沙文態度,當然不能完全同意。可是,這種擁學術傳統以自重的精神,依然是我所尊崇的大學之風,只要治校理念明晰,照樣為我所支持。
不過這些名校近年頗受財務重壓,為了多賺學費,也常常廣開善門,大大放寬招生標準。只希望他們晚節能保,找到能兼顧募款與理念的治校高手吧。
05
於是我申請研究所的方向當然也就轉向一批較年輕的大學,這些大學中,也頗有幾所名氣大、而且電影研究所也夠頂尖的學校。
一般公認美國在電影攝制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幾名,無非就是下列這幾家比來比去——位於好萊塢旁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紐約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我在向這幾所學校索取申請書與學校簡介的時候,就開始發現各校不同的理念,而且各有根據,相映成趣。
拿我後來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來說,我就發現他們雖然每年申請進入電影攝制研究所的人超過六百,而名額只得三十人,但他們在篩選時,卻不重視拍電影方面的經驗,而是以你的創作潛力,做最優先的考量。
這種標準,使得我入學後,發現同班的研究生,分別具備了各式各樣的有趣背景,有念經濟系的、有念法律的,也有念歷史、念人類學的。
加州大學這樣做的企圖很明顯——拍電影這件事,應該登得上學術殿堂,但你從創設期開始,就必須構思:如何擴大電影人的視野、如何使電影的人文基礎更深厚、如何使一家電影攝制的研究所,不至淪落為「職業訓練班」?
加州大學的第一步,就是免除了技術導向的包袱,仔細吸取各領域能為電影再加分的族群。
06
在加州大學的求學過程,當然還讓我見識了各式各樣的大校風範。像該校對我這樣一個外國學生所知不多,就給了我學費全免的優惠;或者天方夜譚般請到影史上第一大師奧森威爾斯駐系指導;或者是全力協助學生做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學態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學生必須擔任電影業中各類職位,並與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強硬原則。

所有這些經歷,都使我相信了大學理念,並非日趨縹緲的空談,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課程設計、靠號召人力、靠資金運用來逐步架設完成的。
我的性格,受困於體制的可能,遠超過受惠於體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學的體制下,我很紮實的受了惠,原因很簡單——那個體制,是一個敦促人良性競爭、成全人自我做到的體制。
大學之所以能「大」,大學之所以能「學」,都源於此。
如果不小心侵權,請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