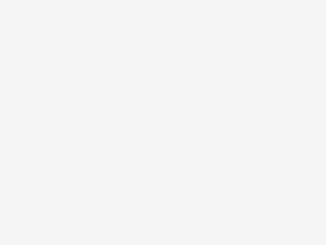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原標題:俞敏洪道歉了,但這個時代的厭女症遠沒結束
「衡量和評價的方向決定了教育的方向,比如,中國女人挑選男人的標準是要男人會賺錢,至於良心好不好不管,所以中國女性的墮落導致了國家的墮落。」
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在某論壇上的講話在網路上引起強烈爭議,尤其是其中「中國女性的墮落導致了國家的墮落」的斷語,令不少網友無法相信,號稱每年讀一百本書的俞敏洪,為何會說出如此歧視性的言論?女星張雨琦更直接開懟。

張雨琦微博截圖
輿論發酵之後,俞敏洪很快在微博上做出了解釋和道歉,表示自己真正的意思是「女性強則男人強,則國家強」。這解釋是否能自圓其說,先按下不表。但俞敏洪絕不是唯一一個持有此類言論的人。
「我只是愛惜女人,才讓女人遠離哲學」
「我只是為你著想,才勸你要遵守女人的本分」
「我只是太喜歡你,不舍你在外受苦,才希望你在家做個賢妻良母」
與這些言論對照,「中國女性墮落導致國家墮落」是不是顯得特別似曾相識了?從此前頻頻爆發的校園性侵害事件,再到時不時刷屏的「女德班」,在每一次涉及性別議題的討論中,此類言論總會隨之出現在我們的視野裡。乍聽之下,它們似乎飽含著對女性處境的無奈甚至愛惜,但細究起來,卻總免不了令人不適的觀感。這種不適,來源於其背後蘊含的「厭女」嫌疑。「厭女」
(misogyny)
,顧名思義,意指對女性的憎恨與厭惡。但這種最為廣泛的基於字面意思的理解,卻未免太簡單粗暴。
實際上,考察厭女運行的機制,我們會發現,與其說它是一種散發的、私人化的心理現象,不如說它是一種系統性的社會機制——置身其中的人,很容易就被卷入到此機制中,卻不一定自知。其實質是對某些刻板性別規範的內化與接受,並進而要求女性去遵守這些「性別本分」,諸如要顧家、要賢惠、要溫柔、要美貌,對那些不滿足此要求的女性,自然生出不滿與厭惡。從這個意義上說,「厭女」實際上比我們想像中有著更牢固也更隱蔽的土壤,它來源於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偏見與歧視。
當我們指出一個人的性別歧視行為時,我們可能需要證明是此人不公正地對待不同性別,而有效的回應也就應該是表明,此人的對待沒有不公正。我們會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往返討論。另一方面,當我們指出一個人的行為是厭女行為時,我們似乎要證明的是,此人厭女、憎恨女人;而似乎,有效的回應就是,「不會啊,他很喜歡女人!」
於是乎,我們常常可以見到,每當周國平們的厭女言論被點出來時
(編者註:著名哲學家周國平先生曾多次論及女性與哲學的問題,表示「學哲學是女人的不幸,更是哲學的不幸」,認為女性不應當做哲學研究,對哲學與女性都是損害,引起頗多爭議)
,他們典型的回應是,「不會啊,我們只是愛惜女人,才讓女人遠離哲學」。每當出現指責某些男人跟蹤、禁錮、傷害女性正是厭女行為的時候,總有聲音回應:不會的,他只是很喜歡女人,所以「為愛情」做了這些糾纏行為。只要是喜歡女人,自然不存在厭女。
如果這樣理解厭女,似乎最終結果便是,除了少數出於憎恨女性的行動以外,大部分厭女行動都可以被重新詮釋成為「出於愛」的糾纏。甚至連續多起所謂「非自願處男」
(「incel」)
暴力殺害女性時,都有人認為,他們實質上是喜歡女性但追求不到而走上極端之路的個別案例。關於厭女的說法,多數就這樣被消解了。的確如此,大部分直男喜歡女人,如何可能是厭女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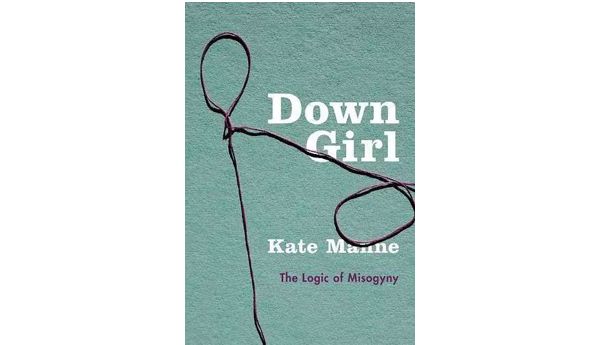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作者: Kate Man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2017年11月
回應這一問題,康奈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凱特·曼尼
(Kate Manne)
的新書《聽話女孩:厭女的邏輯》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在哲學上探討了「厭女」這一概念的實質。曼尼認為,厭女的實質並不是女性的形象出現在男人的腦海中,然後男人對女性充滿憎恨;而是女人出現在男人的世界中,不符合男性中心的要求。換言之,厭女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其實是大男子主義認定,社會中的某些領域,女人本不應該亂闖;女人自有其角色,當她們不守這些「本分」的時候,厭女的作用就是通過敵意打壓女性服從男性中心對她們的規限。也因為這樣,當女性獲得的解放越多,厭女的反撲也就越強烈。
「厭女」就是憎恨女人?
上野千鶴子的名著《厭女》開篇就寫到一個悖論式的現象:喜歡女人的男人為何如此厭女?按上野的觀察和分析,即便是喜歡表達熱愛女性的男作家,他們對女性的描述也充斥著厭女的言詞。喜歡女人的男人,如何可能厭女呢?
「厭女」
(misogyny)
最流行的理解來自於它的古希臘詞源,字面的意思就是對女人的憎恨,對女人的蔑視。也就是說,厭女者僅僅因為對方是女人,而對她保有憎恨、厭惡、蔑視、恐懼等等的態度情緒,然後引起他說出厭女言論或者做出厭女行為。厭女態度和行為都具有統一的心理基礎,這也是上文悖論式現象的基礎:心理上既喜歡女人,又厭惡女人。曼尼將這種常見的理解稱為一種樸素的厭女觀
(the naive conception)
。

《厭女》作者: [日] 上野千鶴子 譯者: 王蘭 上海三聯書店 2015年1月
這樣一種天真粗暴的厭女觀之所以流行,首先在於它看似非常具有說服力:人怎麼會僅僅因為性別而如此對待女性呢?憎恨似乎是最好的解釋,只有足夠的憎恨才能充分說明。另外,正如努斯鮑姆
(Martha C. Nussbaum)
在最新著作《恐懼的專制》
(The Monarchy of Fear)
裡所說的那樣,社會中常見的厭女行為和態度,多數涉及這些負面的心理反應,包括恐懼
(fear)
,責備
(blame)
,厭惡
(disgust)
等等,就算這些未必是厭女的原因,至少它們會伴隨著厭女態度和行為一同出現。不過,仔細分析之後,不難發現這種觀念在哲學上頗有問題。
在知識論上,這種觀念使得關於厭女的知識不可靠。將所有的厭女行為都解釋成厭女者的情緒反應,我們去判斷某人是否厭女時,要麼只能通過他的自述來確定,要麼接受某種弗洛伊德式的難以解釋的潛意識情緒。前者便是很多被指責為厭女者的回應,「不是啦,我只是很愛惜女性。」後者則是一系列不可證偽的不科學判斷。厭女因此變得難以確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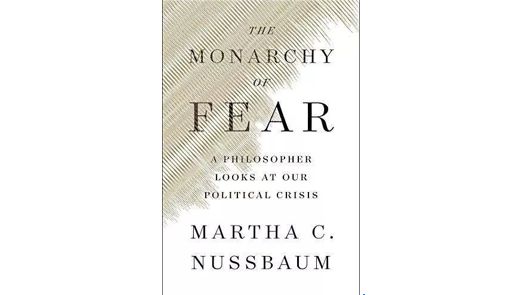
《The Monarchy of Fear》作者: Martha C. Nussbaum Simon Schuster出版 2018年7月
另一方面,這也無視了女性受害者的地位。如果厭女的充分解釋只能是傷害者的心理情緒反應,受害者無法「看到」情緒反應,自然無法知道對方是否真的厭女。這種知識論上的結論是難以接受的,同時在也會導致認知不正義:受害者證言不足信,因為她們的證言不可能是知識。無怪乎曼尼說,「結果,樸素的厭女觀會對厭女的受害者進行消音。」
在形上學上,將厭女理解成一種心理厭惡、恐懼,使得厭女變成某種心理疾病或者僅僅只是某種不理性,這錯誤反映了厭女的實質,忽略了厭女所具有的社會性。厭女被理解為個別的心理障礙,結果往往就是讓厭女者更能獲得社會同情。厭女者做出傷害女性的行為後,輿論上很快就會出現對傷害者大量的同情:他一時心理障礙,愛得太深,這位教授只是想現實地幫助女學生……輿論上的「himpathy」
(作者註:him+sympathy,一個杜撰詞,大意為同情加害者)
常常比對受害者的同情還要強。
綜上可見,這種樸素的厭女觀在哲學上頗有問題,盡管它看似直觀。與其將厭女看成某種心理情緒反應,將厭女理解成一種社會的屬性更能展示厭女作為社會現象的實質。
與其說是心理現象,不如說是社會機制
曼尼認為,厭女是一種社會屬性,不能僅僅通過零散的個體現象完全解釋。女性在社會中需要面對各種不同的敵意,而原因在於她們身處男人的世界之中,並且被認為不能符合男人世界裡的要求。
什麼意思?在曼尼看來,與其將厭女看做一種心理現象,我們更應該將厭女看作一種社會實踐。在一個厭女的社會裡面,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規範:女性應該如何生活?擔任什麼角色?這些規範往往由男性的需要和期待來定義,因為這個是男人的世界。當女人違反這些規範時,社會就會通過各種方式,恐嚇、打擊、懲罰等等,來表達對她們的敵意,讓她們遵守這些規範。比如禁止女性駕駛車輛,製造對女性不友好的工作環境,以及對女性充滿敵意的社會風氣等等。
女性面對的敵意相當多樣,只要作用是打壓女性,讓女性「回到本來屬於她們的位置上」。厭女不再只是憎恨、厭惡,還可以包括鄙視、貶低、嘲弄、侮辱、中傷、妖魔化
(「最毒婦人心」)
、性化
(「婊子」)
、消音
(「女人懂什麼」)
,還有怪責、居高臨下指導、暴力等等行為。這些都是為了壓低女性,讓她們順從的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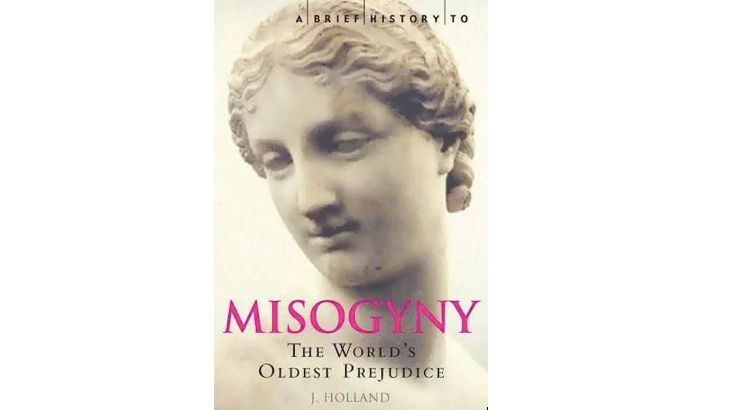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作者: Jack Holland Robinson Publishing出版 2006年7月
厭女會涉及各種不同的心理反應,但我們不需要將這些心理反應看做厭女的解釋,而是厭女的內容。作為社會實踐,厭女行為自然涉及各種敵意,這些敵意盡管看起來是個人關係,但實質上是一種政治現象。在形上學上,厭女是一種社會環境,而非單純個人關係。
厭女並不依賴於個體的厭女者。反過來,厭女者應該被理解為厭女社會中作出厭女行為的個體。厭女不再是零散的個體行為,而是系統性的政治現象。
將厭女理解為社會屬性,可以避免樸素厭女觀在知識論上遇到的問題。首先,厭女現象在知識論上不再深不可測了。它不依賴於個體厭女者的心理反應,我們可以通過更有效的方法得出關於厭女的判斷,比如通過實證比較,先固定其他如種族、階級、年齡等因素,比較相似條件下一個女性和男性參照者所面對的環境,看看女性所受到的敵意,假如男性並不需要面對同樣的敵意,這就可以證明厭女現象的存在。這些判斷都是可證偽的判斷。
另外,這也避免了認知不正義。不再使用傷害者主體的標準,女性可以更合理地提出對厭女行為的詮釋,可以被合理地接受。在判斷對方是否造成傷害的問題上,女性不再被消音。
厭女是如何執行的?
在此種理解下,厭女更像是一種規範規則的執行機制。厭女在形上學上依賴於這些規範的存在,如果一個社會不存在對女性位置的規範,厭女也不會存在。可以說,厭女就是男性中心主義對女性地位、位置、角色的規範和期待的檢查和執行機制,通過各種方式使得女性只可以根據這些規範和期待生活。
而性別主義
(sexism)
就是為這些規範和期待提供辯護的機制,目的就是要合理化男性中心的性別秩序。隨便翻找資料,看看身邊的言論,我們會發現,性別主義者最常援引的正是將性別角色、性別差異自然化的論證。男人天生打拼、女人天生更適合在家照顧育兒照顧家庭;男人天生更理性、女人更天生更感情用事……性別主義的功能正是為了提供性別秩序以辯護。
這樣,性別主義就提供了許多關於男人女人所「應當」承擔的角色的規範,然後,由厭女執行這些規範。

《時代》雜誌將打破沉默、講述被性騷擾經歷的女性作為2017年「年度人物」
厭女通常會區分好女人和壞女人。厭女不是懲罰所有女人,而往往只懲罰那些逾越規矩的壞女人:那些沒有給予男人足夠注意力的女人,那些沒有提供足夠情感支持的女人,那些搶了本屬於男人的學位、工作的女人,那些獨立於男人追求性自主的女人,那些不感情用事的理性女人,那些沒有回歸家庭的女人……無怪乎,所謂「非自願處男」怪責的都是女人沒有看到他,女人本應該給予男人足夠的註目。
厭女也不再必須將女性物化。這是曼尼的書中頗為有洞見的部分。我們常常直覺理解,只有將女性物化,才會出現各種針對女性的惡行。但實際上,物化對於惡行而言,並非必要,也不充分,盡管每每宣傳口號上是各種物化的言論。社會化的認知常常通過更複雜的概念來區分人,將對方看做低於人的物品。我們憎恨、厭惡的往往是那些「敵人」,「叛徒」……而不是物品。因為對方是敵人,所以才對其充滿敵意。
厭女也是一樣,好比美國的狗哨政治,我們聽到「女強人」「女博士」同樣產生各種排斥、嘲笑、厭惡的敵意。厭女的執行,並不需要預設了對女性的物化。反而,正因為女性「過分」的獨立自主自由,使得厭女者更厭惡女性——這些「壞女人」不再遵守社會規範的要求。周國平們可能從來沒有物化過女人,但是他們視這些女人為「不可愛」。
也因為這樣,當女性越獲得解放,厭女也會越強地反撲。
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不正是最好的例子嗎?當越來越多女性CEO出現,往往也伴隨著越來越多對她們的負面輿論,似乎也只有女性才會被要求追求如何兼顧家庭和事業。當女性對追求者提出高要求時,常常會被貼上諸如「高冷」「拜金」等等標籤,似乎女性就必須盡可能地接受男性的青睞,給予男人關注。
反對性騷擾的聲音獲得重視,許多以往不敢發聲的受害者站出來指控騷擾者,我們看到性別平等進步的同時,也看到越來越多質疑,好像所有男人都身處在被誣告的危險之中;女人本來已經足夠平等,現在要反咬男人。那些被指控的男人,也往往很快獲得各種同情:他是某某學者,偶然犯了小錯誤而已;他是優秀的運動員,一時犯錯並應該葬送他的前途。
更好地認識厭女,在哲學上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性別的本質,更好地了解做到性別平等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
作者:劉滿新
編輯:徐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