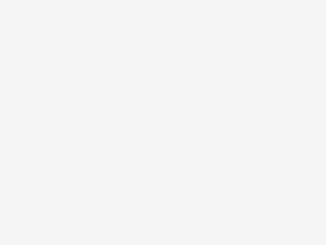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冰點特稿第1119期
上世紀九十年代那些事

1998年,旅客在通遼至集寧的火車上。火車是百姓出遠門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改革開放,讓世代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離開故土,踏上追夢的旅途。王福春/攝

1992年,深圳,人們蜂擁而上搶購股市抽簽表。

1992年8月,深圳以發售認股抽簽表的方式發行5億元新股,一位小夥子排了兩天兩夜的隊,在發售前半小時被清理出列。張新民/攝

1998年11月25日,河南嵩縣車村鎮高峰村,選舉村委會主任的投票結束後,工作人員在統計選票。高峰村83戶農民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委會組織法》,有生以來第一次自己做主,選定村裡的「當家人」。王頌/攝

1991年,海南海口市區,街頭的小攤及租買房廣告。

1993年9月24日凌晨2時27分,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申辦奧運會直播現場,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布的結果驚呆了現場所有人——北京以兩票之差輸給了澳大利亞的雪梨,無緣主辦2000年夏季奧運會。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劉占坤/攝
上世紀90年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它是中國的未來由朦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關鍵年代。正是有了這個改革開放的過渡期,上世紀80年代的價值才會轉化成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行動。
天涯、海角、爛尾樓
1991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張寶全,正興高采烈地準備拍人生第一部商業電影,卻接到八一電影制片廠撤項的通知。「不就50萬元嗎?乾脆自己下海掙50萬元再拍」,張寶全決定到南方尋找機會。
他帶著身上僅有的幾百塊錢來到這個「舉目無親」的經濟特區。「飛機門一打開,悶熱潮濕的空氣向我撲來。第一感覺像是進了桑拿房。」張寶全對深圳的印象並不好,「我本來就怕熱。」但張寶全還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個年代國內很多地方都還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著好鞋子。
為了節省費用,張寶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沒有空調。「我買了一箱泡麵,塞在床下面。」他邊等機會邊找朋友。有一個朋友在深圳倒賣批文和手持式電動縫紉機,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張寶全希望成為第四個人,結束「無業遊民」的狀態。
有一回,老板請了很多主管去唱卡拉OK,這也是張寶全第一次進K房。老板介紹說:「這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高材生。」
「當時我覺得很丟人。」2016年,在北京郊區的別墅裡,張寶全還記得當時的尷尬,「你還不如那個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錢。那時候藝術不值錢,錢最值錢。萬元戶和導演出去,人家滿臉的笑容肯定是給那個萬元戶的。」
後來張寶全在朋友處聽到老板對自己的評價是:張寶全就是個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張寶全只好離開深圳,幾個月後,轉戰另一個經濟特區——海南。
初到海南,張寶全走出飛機門時沒有濕熱的空氣,只有滿耳打樁機的聲音,「咣當咣當」,「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覺得這個地方有機會」。1992年正是海南地產泡沫的頂峰,以四大銀行為首的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要賺錢,到海南; 要發財,炒樓花」。
後來與張寶全並列地產界「京城四少」的馮侖、潘石屹都已經在海南開始原始積累。張寶全剛到海南時,馮侖的萬通正在募資,還有人找過張寶全讓他募股。當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萬,房地產公司就有2萬多家,沒人知道房子蓋好賣給誰。
「那是海南最瘋狂的時候,擊鼓傳花。一個窮光蛋,一夜就能變成百萬富翁。」那時的百萬富翁可以抵上現在的億萬富翁,張寶全親眼看到這樣的神話。一個從北京下海的人,身無分文,借了200萬元,不買地而是買了兩台賓士,專門跑當地主管,請主管吃飯、娛樂,結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來一轉手,就真的有錢了。暴富後這個人回貧窮的老家光宗耀祖,答應幫家鄉政府脫貧,縣裡籌集了2000萬元交給他,他也豪氣地承諾能賺兩三倍。他把錢買了地,卻沒想到海南地產泡沫很快就破滅。
「土地價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負翁’了。」張寶全回憶起這位朋友的慘況,「老家人都說他是騙子,2000萬元對他們老家是要命的,最後老家公安局來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徹底完了。」張寶全說,泡沫時,最慘的就是千萬富翁和百萬富翁,因為他們都在銀行貸了幾倍的錢押在土地上。
剛到海南的張寶全花了很大力氣才註冊了一個房地產公司,「花了一個月時間,把科長、處長都跑了一遍。」張寶全記得,那時候海口沒有公共汽車,「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見,離工商局快100米時就下車,把衣服弄好,然後走進去」。
張寶全記得那時有個「麻科長」,「那個科長滿臉麻子,招待他不僅得請吃飯,還得請唱歌、請跳舞」,一個月下來,錢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個公司就張寶全一個人,「做飯、打字、打掃衛生、總經理,都是我一個人幹了」。當時,「幾乎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到海南做房地產」,投資者多而創業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機構找來談合作,行長助理希望張寶全能幫他們註冊一個房地產公司。剛跑了一個月工商局的張寶全,一個星期就幫他們把公司註冊了。
一天,行長助理帶著四五個人到海口來,「很認真地找我談判,要在海南聯合開發房地產,而我當時就一個人」。談判的條件是:所有項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資,共同經營,共擔風險,共分利潤。
「我當時一聽就樂了,因為我沒錢,共同融資肯定都是他們去籌錢。銀行有的是錢,就是不會幹活,所以利用我來經營。」很順利,雙方簽下了聯合開發合同。張寶全也開始了真正的商業人生。那時已經是1992年年底,離海南房地產泡沫破滅只剩下幾個月。
半年後泡沫破滅時,張寶全已經在海南聯合開發了3個項目。「錢肯定收不回來了,但是資產全在,因為我的合同都寫得好,雖然價格掉下來了,但還沒有變成負資產,至少金融機構沒有損失,只是沒法變現了。正因為這樣,銀行也很感激我。」
在海南時,張寶全還買了一艘船做海運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創業,也是從海運起家。「判斷經濟過不過熱就看船的運價:經濟過熱,這個運價一定漲50%甚至翻一倍,都是貨主在找船,船東天天在家躲著睡覺;經濟不樂觀時,像現在,船東都在到處找貨,還找不到貨主。」
張寶全一邊做海運,一邊做房地產。「剛開始我真正做生意賺錢的是海運,後來房地產開始崩塌,海運公司還支撐了我們的過渡。」
從1992年10月註冊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產崩潰,張寶全經歷了一次經濟危機的洗禮。2萬多家房地產公司倒閉了95%,海南出現三大景觀——「天涯、海角、爛尾樓」。
1994年,張寶全回到北京,重新創業。「南方很市場化,海南對我來說是夢開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訴我什麼叫市場。」當年北京的創業環境還很差,「北京還是雙軌制,在北京做地產,要不就是國營企業,要不就掛靠國營企業,都要靠關係」。當時北京只有10家國有企業有房地產開發資質,張寶全想開發如今位於西直門的今典花園項目,就找到住總合作。但因為換主管等原因,最終沒能成功立項。
張寶全只好轉跟民政部一家有資質的房地產公司合作,但剛蓋完章批下來,這家公司就出爾反爾了。「以他們的名義立完項,他們就想把我踢開,把這個項目賣了,賺一筆錢走人。」張寶全很生氣,「我前面做規劃、買拆遷房,已經花了幾千萬元,那幾千萬元就算擔一半也足以讓我破產。」
後來張寶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訴,說這家公司只有資質,根本沒有開發實力。北京建委後來就批示:民政部這家公司須在兩個月之內打2000萬元保證金到建委帳號,否則撤項。
「1996年,那是房地產最低潮的時候,他們瘋了似的上躥下跳找錢。但這兩個月對我來講,也像判了死緩的感覺。」萬幸的是,對方最終沒有找到一分錢,立項被撤銷後項目終於回到了張寶全手上。
上世紀90年代初的海南市場,培訓了一大批企業家,後來成名的92派企業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經歷過高峰和崩盤。」張寶全說。
深圳「8·10」股瘋
1992年8月,120多萬人從全國各地湧向特區深圳,搶購新股認購抽簽表。他們日夜排隊,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間引發混亂,深圳市政府緊急應對,稱其為「8·10」事件,民間則稱之為「8·10」股瘋。
易駿鵬如今在廣東某事業單位任中層,1992年8月8日前,他還是個跟股票沒半毛錢關係的深圳初中生。8月8日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點就被叫醒。父親叫他趕緊吃早餐出門,「隊伍已經排起來了,到處都是人」。
母親也在旁邊催 :「快點快點,股票不等人啊!」她清點著等會兒排隊要用的東西:水壺、扇子、驅風油,以及找老家親戚借來的10多張身份證。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駿鵬只記得他們把這次排隊看得特別重要,那個暑假不論在家或去同學家串門,父母們都在說一個新詞 :「打新。」
上世紀90年代初,一大批企業籌備上市,上市前會進行新股申購,股民「打新」就是搶最早申購的資格。一般情況下,股票上市後的價格都會高於申購價,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漲的。「打新」確實能賺錢。易家人去排隊時,國內的股票不僅在漲,而且持續瘋長幾個月。
1992年3月,深物業掛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盤價11元,對比前一年10月底發行時的每股3.6元,漲了近兩倍。
上海更熱鬧,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漲停板限制,上證指數(即滬市綜合指數)從前日收盤的617點升到1266點,漲幅高達105%,其中輕工機械漲幅最大,達470%。前所未有的超級牛市中,許多搶占先機的普通人搖身變成百萬富翁,而那時一個內地職工兢業業上班,月薪最多兩三百元。
越來越多人知道股市來錢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應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採用「抽簽」的方式。
8月7日,深圳發布1992年新股發售公告:發售新股認購抽簽表500萬張,一次性抽出50萬張有效中簽表,中簽率約為10%,每張中簽表可認購1000股新股,一共發行國內公眾股5億股;認購者憑身份證到網點排隊購買抽簽表,一個身份證購一張,但每個認購者可帶10張身份證,每張抽簽表100元。抽簽表發售時間定於1992年8月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這次深圳發行的新股上市後價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資1000元買10張抽簽表,除非運氣太差,怎麼都能中一張,中了購1000新股,很快就能獲利萬來元。要是中了簽不炒股,光轉讓抽簽表都能掙一大筆。易駿鵬聽父親說,有人在上海買了300張認購券,算上雇人排隊和租身份證總共成本不到1萬元,轉手賣出,數天淨掙70多萬元。
8月7日的《深圳商報》頭版刊載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個銷售網點的具體地址。彼時的《深圳商報》向全國發售,並因提供經濟特區動態受到全國關注,報紙當天就可以通過航空運達哈爾濱等國內各大城市。加上電台廣播、座機、尋呼機的暢通,無數和易駿鵬父親一樣想在股市發財的中國人,很快確定了消息。
消息靈通的股民更早聽到風聲開始行動。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郵局收到一個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張身份證。當時有關部門可能,大約有320萬張居民身份證「飛」到了深圳,全是用來購買新股認購簽的。易駿鵬一家當時住在羅湖東門,處在深圳商業集中的老城區,占盡地緣優勢。可當他們提前兩天開始排隊,時間剛到8月8日上午11點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擠人,到處都是人,越來越多,越來越擠。」《深圳晚報》編委、知名攝影師趙青回憶時,找不到比「人多」更直接的語言來形容那火爆場面。他用膠片相機記錄了數百個擁擠又無奈的排隊現場。回憶那畫面,趙青欲言又止:「他們拼命地喝水,看著真可憐,那麼多人排隊,希望很渺茫。」
他記得荔枝公園正對面的一個小營業點,為了買新股,在現場公安的引導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個接一個,伸出手臂環抱住前面的人。
「不論性別年齡,不論認識不認識,都前胸貼後背。為了買上股票,什麼都可以不顧了。」易駿鵬感慨。但當時,擠在長隊裡的他才13歲,腦子都是蒙的,渾身難受沒法思考。「怎麼能不難受呢?排了幾天幾夜,困了就擠在那裡睡覺,不敢徹底睡死了,怕被別人擠出來,打著瞌睡一步步往前挪。」他說永遠記得隊伍裡的味道——奇臭無比,大家晝夜排隊都沒洗澡,那些大老遠從外省來的人則可能從擠上火車起,就沒有好好洗漱休息過。
還有不少排隊的人來自深圳、東莞的工廠。一些工廠老板暫停業務,給每個工人幾十元的報酬通宵排隊。工人們沒有邊防證進不了特區,老板就給深圳「二線關」附近的農民塞錢,讓他們帶路鑽鐵絲網避開檢查。多位親歷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員說,當時有約120萬人在全市300多個新股認購網點排起了長龍。
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協調秩序的指揮部,投入七八千警力。「每個點都有公安維持秩序,到9日上午,又加派了武警、邊防戰士。」趙青說。一位前駐深軍人記得,他所在的部隊幾乎全部出動,戰士們手挽手組成人牆,將排隊的人群有序隔開。
秩序維護的需求,起初是由於股民們急迫中簽發財的興奮,後來則是夢碎的失望與憤怒。一些網點開放不到1小時,就宣布抽簽表賣完;一些網點秩序失控,開售時間不斷推後,每晚一分鐘開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開罵網點營業員。股民懷疑有工作人員舞弊,數千人排長隊,只有幾十人買到,黃牛們卻手握一大把抽簽表叫賣,價格比原價高了好幾倍。
偏偏天氣也很磨人。「三十幾攝氏度的高溫,一會兒大太陽,一會兒下雨,人們晝夜排隊,廁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易駿鵬在現場還看到有人昏倒,執勤的公安用瓶裝水澆他的腦門。
熬到又一個天亮,混亂卻繼續升級。8月10日出街的《深圳商報》頭版印著股民們並不想看到的結果——《我市新股認購抽簽表一天發售完畢》,導語強調:「至昨晚9時許,全市300多個網點已全部銷售完畢。」前來上班的網點營業員也一遍遍大聲喊:「沒有了,沒有了。」人們不肯離開,繼續圍著,易駿鵬眼看排了一兩天的隊伍在幾秒內被擠得亂七八糟。
為穩定局面,遠在新疆帶隊考察的李灝(深圳市委原書記、深圳證券市場主要開拓者)提議寅吃卯糧,把次年的500萬股票額度提前發行,8月11日下午繼續發售。深圳市的印刷廠連夜開工加印兌換券,事件才就此穩住。11日下午,人們再次聚集排隊購買可以兌換股票的機會,不眠不休。
深圳股市「8·10」狂熱後,新中國股市出現第一輪熊市,證監會因此成立,人們心中「買股票一本萬利、搶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終於破滅。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公布「8·10」事件調查結果:私買抽簽表10萬多張,涉及幹部、職工4180人。很多親歷者相信,真相可能比這更嚴重。「那一場風波中,算來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易駿鵬開玩笑,他說排隊的股民身上都帶著大量現金,股民們內鬥外鬥,筋疲力盡,小偷不停得手,得手了就去享受。
從村子到「世界工廠」
1994年年初,黎永漢第一次見到火車站。站在人潮洶湧的廣州火車站廣場上,他一眼就看見候車大樓兩側的八字標語——「統一祖國振興中華」。興奮之餘,他拉著湖南同鄉在火車站廣場駐足觀望。
半小時後,他們扛起行李準備去汽車站買票,一掏褲兜,錢包沒了。一氣之下,他和兩個同鄉決定步行到順德找老鄉借錢,「走了一夜,到順德後卻停留了10年」。
1996年年末,晁停向家裡借了200元,邀上幾個同鄉好友去東莞 「打個零工」,順便 「看看世界」。長途大巴在107國道上行駛了兩天兩夜後,終於把他從駐馬店帶到了東莞,「屁股蛋子都麻了」。為了能在東莞謀份工作,晁停已做足準備: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辦身證時硬是給改成了1977年。沒有工廠敢要17歲的未成年人,「正是當年把年齡改成19歲,才有了後來在東莞的快樂時光」。
1992年以來,每年都有1000萬以上外省人來粵打工。上世紀90年代後期,這個數字達到1500萬。加上廣東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鎮地區的人數,廣東流動人口在2600萬以上。
湖南人黎永漢和河南人晁停的經歷,是2600萬外來人口上世紀90年代在珠三角打工的真實寫照。
離開湖南永州藍山的家時,黎永漢去山廟的神龕前拜了拜。「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這也是沒錢。」「現在人人都是去廣東,您老說我賺得到錢不啦。」「沒事,就當碰碰運氣,見見世面,幹幾年就回了」……他對著神龕一通絮叨。
上世紀90年代初還是縣級市的順德是中國民營經濟重鎮。自改革開放起順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場」理念影響,民營經濟風生水起,正如民間俗話,「不找市長找市場」。黎永漢的老鄉當時正在一家民營家電企業打工。
黎永漢進的電器廠在當時被稱為「家電專業街」的新寧路上,上世紀90年代,這條街上的電器行一字排開,宣示著順德「中國家電之鄉」的地位。黎永漢每天工作10個小時,有時會加班到夜裡9點。在裝配車間,他每天面對的是成百上千條滾筒線,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時時提防空調成品錯位。
「那時的流水線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憑人力,哪像現在都搞什麼人工智能。」白天調試電器,夜晚沖涼睡覺,生活枯燥卻也簡單。第一個月黎永漢拿了400元薪水,他給家裡寄去一半。兩年後他升職做了車間組長,薪水漲了100元。那是1996年,從那年起他也開始作為「老人」,給湖南新來打工的老鄉介紹工作。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隨大流」來到東莞,他也許現在還在駐馬店市泌陽縣割草、喂牛、養雞、種地。「當時身邊人都出來了,問去哪裡,回答都是廣東,說那裡機會多,錢好賺。」
據他介紹,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駐馬店,家家戶戶仍以務農為主。許多年輕人家境貧寒,但憋著股勁兒要去南方看看,於是從駐馬店步行到廣州、佛山、東莞、中山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幾個月,就沿著鐵軌走。」一列列火車飛馳過後,這些年輕人就撿從火車上扔下的殘食充饑。
由於一無所長,晁停最初和同鄉在東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帶入派出所,原因是沒有暫住證。1984年,深圳正式實行暫住證制度,對非本地戶籍人口進行管理。
上世紀90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經濟迅速崛起,但也出現因查暫住證而導致的各類社會事件。2015年2月,中國正式廢除暫住證制度。「大卡車拉了一車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牆站,一個個審問。」不過晁停是幸運的,由於審訊者是河南老鄉,對他的審問也就不那麼嚴格。幾天後他重獲自由,托老鄉介紹進了東莞138工業區的一家造紙廠。
由於薪水過低(200元/月),半個月後他就辭職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為他談攏了一樁親事。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從駐馬店再次出發,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達廣州後,兩人前往流花客運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欖鎮。晁停還記得那輛中巴車裝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剛上車,車門便立即緊閉,隨後他看見幾個戴墨鏡的男子邊吸煙邊抖腿。對方呵斥他「交包交錢不殺」,晁停這才意識到這是輛黑車。
「上世紀90年代這種黑車遍布珠三角,上車就得交錢包。」那次不愉快的黑車經歷後,晁停在中山待了幾個月,「什麼也不會,很多流水線上的技術活兒都不會」。於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顧女友反對,回到了朋友和老鄉眾多的東莞。「老鄉多就是感到踏實。」
回到東莞後,晁停進了位於東莞塘廈的利峰玩具廠。當時東莞憑借廉價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條件吸引著港商的進駐。「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模式助推東莞迅速成為「世界工廠」。
晁停進入利峰的第一個月便感覺不對勁。進廠時對方承諾的薪水不光無法兌現,甚至根本不發薪水,只是為員工提供夥食和住宿。晁停當時覺得氣憤,但卻驚訝於其他工友的沉默。「漸漸地我和他們一樣,也懶得去找工廠問了。」
黎永漢在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轍。「電器廠開始拖欠員工薪水,到最後就完全不給了。」
珠三角的不少工廠在上世紀90年代面對員工討薪時,先安撫並滿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幾個刺兒頭的要求,隨後迅速辭退討薪鬧事的普通員工。不得不說這一招效果甚佳。
晁停入廠不久,發現廠區越發變本加厲:員工被限制在工廠區域內活動,工廠全天候大門緊閉,不允許任何工人出廠。晁停特別氣憤,隨後和幾個同鄉一道翻牆,逃離了那個在他記憶裡形似牢籠的玩具廠。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過老鄉介紹進入一家玩具廠。「那倒是家正經的廠,好幾千號人呢。」在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廠裡,他被分配至噴漆部,負責給玩具噴漆加工。當時他每月能領到500元的薪水,「待遇上去了,生活質量也得跟著提高」。隨後他入手一台300多元的尋呼機,別在腰間威風凜凜。
「其實就圖一好看。說實話,上世紀90年代的車間都是很苦的,流水線上的活每天得幹到晚上10點,哪有時間玩尋呼機啊!有人呼我也沒空給他回啊!」
兩年後,晁停和女友雙雙辭職,回老家駐馬店結了婚。2004年,他們重返珠三角,不過這次不再是回東莞,而是去佛山。「快40歲了,做不動流水線啦,不過真懷念打工的上世紀90年代,騎著變速山地車亂跑,嚼著口香糖打著響指去泡妞,每月薪水全部花光以後一身輕鬆,這些都是上世紀90年代才做得出來的事情。上世紀90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
「現在村裡再有年輕人出門打工,人家會看不起你哩。」晁停說。與上世紀90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開始人才回流。「新聞裡天天說農村空心化,我看就不準確。上世紀90年代的農村確實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發展起來的農村反而留得住年輕人。」晁停說。
黎永漢不這樣認為。上世紀90年代初他從永州藍山前往廣東打工。20多年過去了,他所在的鄉村還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為主。「上世紀90年代早就過去了。一切都變了,一切也都沒變。我反正打算繼續在廣東打工,哪怕經濟環境再艱難,總比待在老家好吧?」
(本文摘自《我和我的九十年代》新周刊編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鄺新華 蘇靜 趙淥汀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