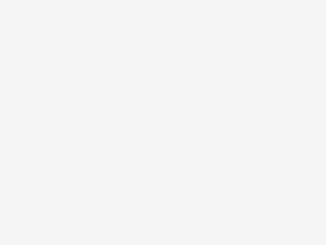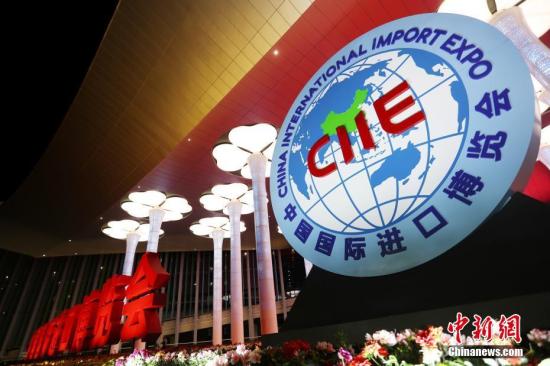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學校恐懼症」在日本蔓延

調查顯示,接近80%的「不登校」學生有遭遇校園霸凌的經歷。

為了幫助「不登校」的孩子學習,教師工藤拓哉開設了帶小隔間的活動室。

日本「不登校」的小學生和初中生已達在籍學生總人數的1%。
在推特網上,日語標籤「不上學並非不幸」正在收集話題。標籤的說明寫道:8月19日,一場「不登校」學生聚會在日本100個地點舉行。活動發起人是24歲的小幡和輝,他希望此舉能讓社會對不願上學的孩子抱以更多同情和理解。「9月1日是自殺的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寫道,「你不必到學校赴死。」
——————————
「我只在夜裡一個人出門」
7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了2018年度《問題行為/拒絕上學研究報告》,這份報告顯示,該國每年缺課30天以上的小學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達13.3萬人,占在籍學生總人數的1%。按一個班級30人計算,這意味著超過4300個班級空無一人。
近20年來,日本中小學就學人數持續下降,「不登校」情況以每年增加近1萬人的速度連年惡化,小學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過初中生(4.9%)一倍;13萬名逃學者中,超過一半是長期缺席。
「不登校」是日本一個獨特的概念。根據文科省的定義,處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每年缺勤達到30天,就被記為「不登校」。不同於家庭貧困或傷病等被動缺席,「不登校」是學生主動地長期逃學。
早在1941年,教育學家就提出了「學校恐懼症」概念。上世紀50年代早期,「拒絕上學」現象開始頻繁見諸報端。彼時日本經濟已進入高速增長,貧困不再是孩子上學的阻礙,「不登校」背後是「中產階級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問題」。
教育網站「東京家學」總結了7種類型的「不登校」:母子分離造成不安型、情緒混亂型(情緒低落,頭疼肚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對學習提不起興致)、人際關係型(恐懼校園霸凌而拒絕上學)、應激性精神障礙型、發育障礙伴有學習障礙型。過去,「不登校」只發生在小學和初中,現在高中和大學生也會「不登校」。
不上學的孩子們在幹什麼呢?很多人宅在家中,整日埋頭於動漫和遊戲。「那個時候的生活基本就是晚上起床、白天睡覺。」30歲的山口真央對日本雅虎新聞網回憶道,「我看電視劇,看深夜動畫,在網上和人聊天。我只在夜裡一個人出門,白天就在房間裡待著。」
相較之下,山口的生活至少算安穩。不少孩子淪為「隱蔽少年」,流落街頭、無所事事,甚至卷入勒索和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受困於嚴重的心理問題,最終走上了自殺的末路。
校園霸凌與「黑色校規」
面對這一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日本社會起初的反應並不令人意外:孩子不上學?打一頓就好了。那時,家長和老師都相信不上學是因為懶散或者不夠勇敢,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不登校」孩子承受了更多壓力,結果適得其反。上世紀90年代,幾乎每年開學季都有學生自殺的新聞傳出。
日本政府和社會開始痛定思痛。他們發現,很多孩子不願上學並非是厭惡學習,而是受制於種種外部因素,其中校園霸凌首當其沖。文科省的報告顯示,近80%的「不登校」學生有遭遇校園霸凌的經歷。
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一些孩子處理不好與教職員工的關係;33%的孩子無法適應學校的社團活動,為躲避這種半強制性的集體活動,乾脆不上學;少部分人因為在讀期間懷孕而被學校勸退。
與校園霸凌不相上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太過嚴苛的校規。在日本,「黑色校規」已成為社會問題。一些學校禁止學生吃午餐時交頭接耳。廣島縣一所初中規定,午餐剩飯的人要被全校廣播點名批評。雖然文科省竭力改變這一狀況,但效果並不理想。2016年,巖手縣一名初二男生因被教師欺負而自殺,而該校是文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範校。
據日本《東洋經濟》周刊報導,2017年9月,大阪一名高中女生因發色被學校勸退,一怒之下將學校告上法庭。這名女孩的頭髮天生是棕色,老師要求她染黑,否則就退學。
一些學校甚至對學生內衣的顏色進行規定,並且由教職員工監督檢查,結果導致了不少性騷擾案例。據「不登校新聞」網站報導,今年3月8日的一項調查顯示,1/6的日本初中對內衣顏色有要求,其中相當一部分學校會進行檢查;曾受到教職員工性騷擾的學生比例為1.9%,這意味著每兩個班級中,至少有一人曾被教師動手動腳。
試圖獲得父母更多關愛,也是孩子們「不登校」的原因之一。日本沉重的生活壓力下,很多父母既無時間也無精力照顧孩子,使得孩子以出格的方式獲取關注。「我想多看看父母,我一天也沒機會跟他們說上幾句話。」曾經的「不登校」兒童棚園正一告訴日本《朝日新聞》。
還有些人純粹反感上學。「學校就如此重要嗎?」有人在「不登校新聞」上匿名寫道,「我現在30多歲了,依然不理解為什麼必須上學。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我總是很痛苦。當然,我知道學校存在的意義,但我不適應學校的‘框架’……為什麼我不能做想做的事,要像個奴隸一樣被困在學校裡?」
他們為幫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
討論「不登校」問題的同時,日本社會積極探討解決之策。教師家訪、單獨輔導等措施是「標配」。櫪木縣宇都宮市從2007年開始實施「缺勤一天就打電話,連續兩天就家訪」政策;名古屋市在網上公布了詳細的「不登校對策基本構想」,目標是在追蹤孩子心理狀態的同時,減少父母的焦慮並給予支持。
一些人盡其所能,為救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據《朝日新聞》8月7日報導,43歲的教師工藤拓哉在石川縣金澤市開設了名為「每個人的位置」的活動室,配有平板電腦、無線網路,還有從小學到高中的試卷和習題冊。房間隔出了一個個獨立空間,孩子們不必與他人接觸。
為了告訴孩子們「你不是一個人」,減少他們的孤立和絕望感,並提供更多出路,專門的信息管道被建立起來。「就算不去學校上課,也能參加高中入學考試,這樣的先例很多。我認為,得知這一點會令你的焦慮消失。」小幡和輝對「不登校新聞」說。
今年5月,這家日本最大的「不登校」新聞網站慶祝了成立20周年紀念日。編輯部中,不少人本身就有這種經歷。「高三時,我逃學了。我很害怕,根本離不開家,花了將近一年才好起來。」21歲的水口真衣告訴雅虎新聞網,「兩年前,一個電視節目提到了‘不登校新聞’,我征求了母親的意見,於是一個月後,同齡人出席高中畢業典禮時,我已經在參加這家網站的編輯會議了。」
「我沒有試圖消除這段痛苦的回憶。」水口說,「我想把它當作經驗,告訴所有為學校而苦惱的孩子,你不是一個人。」
很多人呼籲社會給予更多的寬容。東京地方議員海津敦子在美國《赫芬頓郵報》日本版上發表《逃學不是問題行為》一文,她寫道:「我們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開開心心的嗎?誰都有沮喪的時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樣……讓他們返回學校並非唯一目的。孩子們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路。」
寬容和理解對孩子至關重要。「當我不上學時,最不愉快的事就是聽到母親問:你今天想做什麼?」山口真央說,「每當我聽到這句話,就會情緒失控地說,我知道我必須去那裡!但又沒有勇氣對母親發火,只能盡可能不去看她的臉。」
24歲的楢崎唯對此感同身受。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她就不上學了,最糟糕的回憶是受抑鬱症折磨時,父母卻告訴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不只是你。」「哦,連父母都不承認我的痛苦……我哭了。」她對《東洋經濟》說。
「自由學校」成為紓困之道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民間團體把「不登校」的學生集合起來,通過私人教育讓他們得以繼續讀書。政府肯定了這種做法,並幫助其轉型為財團法人,以便獲得財政補助,就讀的學生也能取得有效的學位證明。
進入2000年,這類機構愈發勃興,被統稱為「自由學校」。它們培養的一些學生經過短暫磨難後重回正軌,甚至有自由學校的畢業生考上了東京大學。
日本第一所自由學校是奧地圭子於1985年創辦的東京新宿學校,後來「轉正」為東京新宿葛飾中學。該校在日本名聲卓著,首相安倍晉三曾於2016年到該校訪問。
距離葛飾中學不遠的新宿大學也是自由學校,小幡和輝就畢業於此。該校校舍是一棟普通的兩層小樓,大學部在地下一層,二樓是中小學,一樓則是辦公室和活動室。大學現有4名職員,40名學生從16歲至23歲不等,教師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當學生們需要學習某一專業時,新宿大學就邀請他們認為合適的人前來指導。
這所學校學生不多,課程範圍廣泛,包括哲學、人類學、音樂、戲劇、法律、歷史、電影等。不過,新宿大學的畢業資格不受政府認可。這裡沒有固定的學制和畢業年限,校方經營除了收取學費,還要靠學生各盡所能,比如學習戲劇的學生定期演出劇目,售賣門票。
「那些學生非常閃亮和活潑,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署名「息子」的母親在博客中寫道。
然而,自由學校非萬用靈藥,首要的問題就是供不應求。日本約有3萬所小學和初中,自由學校則不到500所,遠遠滿足不了「不登校」學生的需求,費用也不菲。據「不登校新聞」調查,自由學校平均每年收取學費4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何況,相當一部分孩子根本不願出門見人。
在日本,「無法適應集體生活」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不登校」的孩子在升學和求職中都會遭遇重重歧視。「不上學是不被允許的」「去自由學校的是弱者」「除非你回去上學,否則沒有未來」,這些聲音都在折磨孩子們本已脆弱的神經。
2017年9月1日,東京上野動物園發聲支持「不登校」的孩子們。動物園在推特上貼出亞洲貘幼崽的照片,並配文道:「亞洲貘遇到敵人時,會一溜煙躲進水裡。逃跑是不需要誰來許可的,請不要顧忌旁人的眼光,有必要就逃跑吧!如果無處可逃,歡迎來動物園。這裡有很多不受人類社會束縛的動物在等你。」
(摘自《青年參考》報2018年8月16日12版)
《青年參考》特約撰稿 袁野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