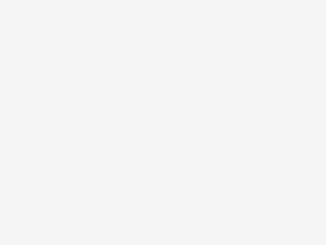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 走近一戰華工後裔,追尋14萬華工的背影 |
| 稿件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草地 |
|
|
|
翻拍照片:2008年11月,程玲一家在法國為爺爺畢粹德掃墓時所攝畢粹德墓碑。記者王陽攝(拍攝時間: 10月30日) |
|
|
|
|
一戰華工正在裝卸貨物。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攝 約翰·德·露西提供 |
|
本報記者鄧衛華、王陽
2018年11月11日,一個值得國人銘刻的日子。
百年前的這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戰以英法等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與英法等國的戰士一起歡呼這一勝利的,還有一群作為「戰勤」與他們一起「並肩戰鬥」的東方人——總數高達14萬人的一戰華工。
遺憾的是,他們的不朽功勛在次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被漠視了。中國作為戰勝國提出的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要求被無情地拒絕,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百年過隙,一戰華工群體已經鮮有存世者。最近,記者走近他們的後裔,觸摸他們留下的珍稀物件,撫讀他們在烽火歲月中留下的珍貴日志與記錄,穿越百年去感受他們不朽的功勛……
90年後,孫女終於找到爺爺在法國的墓地
對於程玲來說,屬於她與華工爺爺的有限物質存在感,只有一枚褪色的銅質勛章。勛章上一位勇士手執短劍,腳跨駿馬,馬蹄下踩著一個骷髏。勛章的側面有一個編號——97237,這是爺爺畢粹德的「名字」。百年時光磨洗下,黃藍相間的勛章絲帶線已經斷開。
在濟南市信義莊西街附近的一個小區裡,60歲的程玲告訴記者,她的爺爺畢粹德原本生活在山東省萊蕪市牛泉鎮一個平靜的小村子——上峪村,可遠在萬里外的一戰戰火,讓他背井離鄉,前往法國在英國軍隊當了一名勞工。
「我從來沒有見過爺爺,他走的時候,我的父親才幾個月大。」程玲說,「我們村裡去了11人,只有爺爺沒有回來。」
百年前的畢粹德,在邁出村子前往法國之前,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命運竟然會和波瀾起伏的世界形勢緊緊聯繫在一起。根據當時中國政府的「以工代兵」計劃,從1914年7月28日一戰爆發,到1918年11月11日戰爭結束,英法等國共從中國山東、河北、江蘇、天津等地招募了14萬華工漂洋過海到達歐洲,進行艱辛的戰勤工作,華工中有近七成來自山東。
「我經常讓父親講爺爺的故事,可他知道的也不多。多少年以來,這枚勛章是我們家人思念的唯一寄托。雖知爺爺早已命喪歐洲,下落蓋不知曉。但是1990年父親去世以後,家人更加念念不忘杳無音信的爺爺,也增加了我們查找爺爺下落的決心。」程玲說。2007年的清明節,她曾在山東當地的報紙上發文,表露了這個家族心願,文中寫道「爺爺,我該怎樣祭奠遠在法國的您?」
讓程玲和家人沒想到的是,正是她的這篇文章,讓法國華僑和留法華工後裔了解她的故事,並伸出了援助之手。讀到這篇文章的張捷哈是老華工張長松的第10個兒子,他的華工父親一戰結束後留在了法國,在二戰時又成為軍人為爭取法國自由而戰,而他本人也曾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他的兒子也曾是法國軍人。「他當時拿著我寫的文章,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並以三代軍人的名義給前法國總理拉法蘭及法國退伍軍人部寫信,最終促成了我們的法國之行。」程玲說。
2008年一戰結束9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幾經輾轉,在英國墓地管理委員會的幫助下,程玲和丈夫、女兒終於找到了畢粹德長眠於法國索姆省博朗古村的華工墓地。擺上家鄉的煙酒、點心、冬棗、高粱飴、芝麻餅,燒紙、點香、磕頭,口中不斷默念——程玲一家用家鄉最傳統的方式,告慰從未謀面的爺爺。
「即便已經找到爺爺的墓地,我還有一個心願沒有完成。」程玲告訴記者,「當時父親剛出生,家裡條件也不算差,奶奶也多次挽留,為什麼爺爺還要毅然決然去歐洲做勞工呢?我想找到塵封的檔案,了解那段歷史。」
開眼看世界的「艱辛之旅」
山東省濰坊市臨朐縣城郊,57歲的馬京東經營著一家規模不大的鋼管廠。在馬京東辦公室的書櫃裡,存放著一個不起眼的包裹。
「這是俺爺爺的照片,這是他的名片,這是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記日記的小本本,這是帶回來的明信片,這是他寫的《遊歐雜誌》,記錄當時的經歷。」馬京東打開包裹,一一介紹著存放了百年的華工爺爺馬春苓的遺物。
馬京東10個月大時,爺爺就去世了。對於馬春苓參加一戰的那段經歷,他是從這些老物件以及家人的口述中了解到的。1917年10月,臨朐縣胡梅澗村村民馬春苓和同村11名村民報名參加英國招募華工活動。按照《招工合同》,工人們每月可以領到12塊大洋,他們在中國的家屬每月也有10塊大洋的養家費。
對於那時普通中國人來說,這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很多華工寄希望以此緩解家中的經濟壓力甚至改變命運。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是常年研究一戰華工的權威專家,他介紹,華工主要來自農村,絕大多數目不識丁、淳樸老實、任勞任怨,渴望能到法國過上更美好的生活。被招募的華工中有一部分是軍人或當過兵;另外很大一部分是技術工人,包括木匠、鐵匠、機械師等;甚至還有一部分華工曾在中國擁有體面的工作,如教師、助理等。這些人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尤其是盼望在西方世界獲得一些新知識。
馬春苓就屬於後者。作為一名鄉村小學教師,他「朝夕講誦地理,而授者聽者,皆恍惚無證」,去歐洲不僅是為了賺錢,也是為了圓自己的「環遊之志」。
同為鄉村教師的華工孫幹來自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域城鎮和尚房村,在他8萬多字的《歐戰華工記》中也表達了他遊歷歐洲考察教育的初衷:「尤以非身臨英、美、法、德其境,以觀察之,不足以明其教育之真諦也。」
然而,想要成為英法雇傭的勞工,競爭異常激烈。據《紐約時報》1917年2月的報導稱,只有「那些經過層層篩選之後留下的華工」才有機會前往法國,其中「大部分人」身高超過六英尺。
法國和英國都想招到身體素質最好的華工,因此都把華北地區特別是山東作為主要招工地,因為山東人體格強壯,吃苦耐勞,並且能習慣法國的氣候。
一位英國軍官這樣描述華工招募現場的場景:應征者「在接待處的棚子中經過分組後被依次帶入位於兵站中央的一間屋子,在房間裡,應征者們脫光衣服,全身赤裸,並按統一的方式接受英國軍醫們的仔細檢查。應征者可能會因為21個原因中的任何一個落選,包括肺結核、支氣管炎、沙眼、瘧疾和牙齒不好等。」
經過體檢、剪掉辮子、清洗全身、再次體檢後,入選的華工每人領到一個刻有身份編號的銅手鐲和一套乾淨的衣服。就這樣,畢粹德、馬春苓、孫幹等14萬華工開始了他們的「艱辛之旅」,一部分華工途徑蘇伊士運河或者好望角到達法國,而大多數則是跨越太平洋,穿過加拿大,再橫跨大西洋前往法國。旅程充滿艱辛,華工不僅要忍受波濤洶湧的大海,還要面臨德國潛艇的威脅,最終抵達一戰西線戰場。
西線戰場上的「中國苦力」
1917年12月,在經歷兩個多月的漫長征途後,運載著3400多名華工的客輪抵達法國,馬春苓很快被分派到了北部加來省一家工廠負責運輸木材。他在日記中寫道:這裡距離「戰線尚百餘裡,故未冒子彈之險,未遭顛沛之苦。」即便是這樣,華工依然能嗅到硝煙的味道,甚至面臨來自炮擊轟炸和毒氣彈的死亡威脅。
馬京東念到一段爺爺不敢脫衣就寢的文字:「彈殼如雨,為害最烈,故各營之中皆備地穴或沙屋以避之。如炸彈擲下,離之五十步或能無恙,一夜之間常奔避數次,故在該地駐七八月,未嘗解衣而寢。」
孫幹曾作詩一首描述頭頂戰鬥機橫行的日子:「一日遷徙二日挪,隆隆雷電何其多。偉大蜻蜓蔽天日,尾瀉青煙快於梭。空中行列如蟻卵,時遭焚毀遇天火。」
盡管身在混亂、時而危險的工作環境中,常常被西方人蔑稱為「苦力」(coolies)「中國佬」(Chinks),華工們仍然創造了巨大的功績。一本由英國軍方1918年編寫的《關於華工的信息》的小冊子稱,中國人「吃苦耐勞,心靈手巧,如果管理得當,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他們的能力令人驚訝。」
了解華工們的日常工作,英國人約翰·德·露西珍藏的照片更加直觀。2018年10月底,一場在山東威海召開的一戰華工學術研討會上,記者見到了這位一戰英國軍官的後代。「我爺爺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是一名一戰軍官,他漢語流利,與中國勞工軍團共處了三年。2014年,我在倫敦家中偶然發現十幾張玻璃幻燈片,這些爺爺拍攝的照片上的主角正是中國勞工。」露西說。
在這些珍貴的老照片上,華工們在歐洲戰場從事著多種多樣的工作:挖戰壕,修鐵路,裝卸貨物,在火藥廠、兵工廠、化工廠和造紙廠等地方工作,有的華工甚至成為修理坦克、飛機的熟練工。
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了大約1500天,但是對於許多華工來說,他們的戰爭記憶是更為漫長、恐怖的,因為他們戰後還要留下打掃戰場,埋葬死者。「戰後有成千上萬被廢棄的炮彈,”華工軍團”的任務就是清除那些尚未爆炸的炮彈,這非常危險。」露西說。
許多為英軍服務的華工在法國一直工作到了1920年,而大部分為法軍服務的華工做到了1922年。迄今為止,歷史學家尚不確定戰時究竟有多少華工在法國為協約國的事業獻身。徐國琦說,可以確信,由於敵軍炮火、瘟疫和傷病,至少有3000名中國人在歐洲或是去歐洲的路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據上峪村華工後裔回憶說,程玲的爺爺畢粹德戰時擔任炊事員工作,在野外做飯時被炸彈炸死。與畢粹德埋葬在一起的華工多為同一天去世,程玲推測他們可能是同時犧牲的。
文明的衝突與融合
在一戰期間,此前甚至很少踏出自己所居住過村鎮的華工們,一步來到被稱為西方文明中心的歐洲,但文明的西方此時卻陷入可怕的戰爭泥淖。面對文化衝擊,他們所看到的一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新鮮而陌生的。食物、語言、習俗等等,都是全新的挑戰。
「在營盤,二十五人一頓一桶飯,一人僅分小半碗,菜蔬蔥地蛋(土豆),有肉常缺鹽,分回吉司(芝士)各數天,飯量大的餓得頭暈眼花沒人管。」孫乾的孫子孫光隆年幼時與爺爺生活在小山村和尚房,孫幹經常會教他唱自己空閒時寫的華工歌或打油詩,這首飯食歌講的就是華工吃不飽的無奈。
「我爺爺說中國人吃苦耐勞,一天能頂四五個外國人的工作量,能幹也能吃。」孫光隆說,戰時,英法都面臨著嚴重的食物短缺,甚至不夠供應作戰部隊。華工愛吃主食,飯量較大,加之西餐不適應,一頓只能吃個二三成飽,「肚腹初嘗食物,食欲方興,食物已罄,疾苦之腹更痛。」
思鄉之情一直在華工中蔓延,最令他們沮喪的還是無法向西方人表達自己的想法。當時一位基督教青年會成員記錄道,「不論我走到哪裡,只要他們發現我會說漢語,都會一成不變地問我兩個問題”現在哪一邊打贏了?”還有”我們什麼時候能回中國?”
學者研究發現,基督教青年會在用教育、體育、娛樂等方式豐富華工生活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透過老照片,可以看到華工們帶有中國特色的業餘生活——跳秧歌、玩雜技、摔跤、舉辦風箏比賽、戲曲表演,甚至用炮彈殼製作花瓶,形成了讓西方人驚嘆的「戰壕藝術」。除此之外,在基督教青年會進入華工生活不久,華工們就學會了踢足球、打排球、玩跳棋、拳擊、下國際象棋等等,這些體育項目讓他們鍛煉身體,更教會了他們歐洲人如何在戶外享受生活。
孫幹就曾在法國協助基督教青年會教育華工。「爺爺是華工中為數不多的文化人。他不光利用戰爭間隙為不識字的華工代寫家書、記帳、起草訴狀,發現華工沾染賭博習氣,便以《告白書》形式勸解同胞。他自己還身體力行舉辦培訓班,教華工學中英文。」孫光隆說。
歷史學家認為,華工在歐洲的經歷可以被視為一次受教育的歷程。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這裡學會了識字和閱讀。他們抵達法國時,華工中的識字率只有20%,但到1921年,已經提高到38%。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了新的思維方式,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919年9月15日,孫幹回到闊別了兩年多的老家,開始整理自己在法國的勞工經歷和觀察到的一切,形成書稿。生於耕讀之家,完成歐洲教育考察的他更加堅定了自己教育救國的理想,繼續在小學任教,成為一位富有實幹精神的平民教育家。他認為,「先進之國家,必有先進之科學,欲有先進之科學,必有先進之教育。」
「我的爺爺從歐洲回來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救國思想,生於內外交困、風雲際會的時代,他作為一個平頭百姓能做的並不多,但是現在看已經很先鋒了。」孫光隆介紹,為了開化民智,孫幹在工作之餘還在趕集的山道上擺攤,教往來路人識字,並和妻子自費創辦了博山第一所鄉村女子學校,這在當時受到村民的歡迎。而同年回到臨朐縣胡梅澗村的馬春苓不但繼續教書育人,還讓家中女人不再纏足。
一位名叫傅省三的華工這樣寫道:以前華工只知道女子纏足為美,現在看見了西洋女兵、女農、女醫等因為天足可以與男人並肩工作勞力,才意識到以前的想法錯了。「一輩子教書育人的爺爺可以說是當時的鄉賢,他”下歐洲”回來後身體力行教育了我們後人。桃李遍天下,非常受人尊重。爺爺去世的時候,來告別的隊伍長達二三百米,從家裡一直排到了村子口。」馬京東說。
旅歐不僅開闊了他們作為教育者的眼界,為農村掃盲、育人、培養了大量人才,更讓他們很多人成了愛國者。1937年,日軍占領博山,時任小學校長的孫幹堅決拒絕出任博山縣維持會長的要求,投奔沂源解放區,參加了共產黨的抗日救亡工作;馬春苓送自己18歲的長子馬傳宗參軍報國,兒子最終犧牲在淮海戰役戰場上。馬京東說,概括爺爺的一生就是他經常說的那句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戰後,華工招募國開始擔心14萬華工作為西方文明的詮釋者將如何講述他們眼中的歐洲,但是中國的社會精英們則對華工的覺醒歡呼雀躍。除了為鄉土中國帶來積極變化,回到城市中的華工也展現了自己的新精神。
1919年9月,歸國華工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歸國華工工會,每周召開一次會議討論如何維護自身權益。這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現代工會之一,擁有約1600名成員,都是剛從法國回來的華工。徐國琦說,華工們知道,他們必須自己為自己的目標奮鬥,自己拯救自己的命運,而他們的行動或多或少得益於在歐洲的經歷。有學者認為,那些「中國勞工世界暴風雨中的海燕」在歐洲的經歷,使他們在上海工會的組織化以及罷工運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華工參與並見證了一戰,我們有話語權來探討戰爭與和平」
「吾十餘萬華工,離祖國,涉重洋,冒鋒鏑,歷艱險,出生入死,參加歐洲大戰,以博無上之榮譽,此實為吾國外交一頁光榮史也。」時任華工翻譯的顧杏卿在《歐戰工作回憶錄》自序中如此寫道。
站在一百年後的今天,華工後裔以至於中國人應當如何看待一戰華工?
2008年,程玲在法國為爺爺掃墓時,法國歐華歷史學會華僑曾作詩:今朝祭拜了心願,歷盡滄桑友誼珍。喜淚飛流同振奮,中華崛起發豪吟。「在爺爺長眠的墓地裡,華工墓碑上刻著”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盡瘁””雖死猶生”等字樣,雖然我現在連爺爺的模樣都不知道,但是他們捍衛文明和自由的經歷已經被歷史記住了。」程玲說。
「我認為爺爺他們那些華工是偉大的一代人,他們參與了一戰,流血流汗地參與拯救了歐洲,某種程度上他們就代表了中國。」馬京東說。
露西退休後,講述華工故事、還原華工歷史成了他新的工作,「華工是一群在一戰中被遺忘的人,他們在西線戰場從事艱辛的工作卻又默默無聞。我公布爺爺拍攝的這些照片就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為西方文明所做的貢獻。」
盡管華工被稱為苦力,但是人們逐漸意識到他們不僅吃了苦,還有巨大的影響力。徐國琦認為,因為華工,中國讓英法等國免於人力資源破產的風險,參與拯救歐洲,向世界展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願景和能力,同時,中國由此可以向德國宣戰,名正言順地成了一戰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義正詞嚴地要求國際社會主持中國公道。
14萬華工就是14萬使者。美國出版的《中國留學生月報》在1918年宣布,華工是中國連接世界的橋梁。「西方一直認為一戰奠定了現代國際體系,比二戰都要重要。一戰結束後,西方一直在反思,為什麼人類要爆發這麼慘烈的戰爭?而中國華工參與並見證了一戰,我們有話語權來探討戰爭與和平。」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關係史研究室主任張俊義說。
近年來,從學術界到政界,東方或西方,華工的歷史意義越來越受到認可,紀念華工的活動受到更多人關注。
去年11月,歐洲首座一戰華工雕像在比利時波普林格市揭幕;英國也在紀念一戰停戰99周年的正式活動中首次紀念一戰華工;今年9月,一戰華工雕像在巴黎裡昂火車站落成。2018年年初,法國總統馬克龍曾向一戰赴法華工致敬,表示「在這苦難的時刻,他們是我們的兄弟」。
在和尚房村的山間墓地裡,孫光隆和妻子帶著比利時博普林格市政府贈予的紀念牌來到孫幹墓前祭拜;而此時,馬京東和程玲正在8000公里外的歐洲參加一戰華工史料圖片展,重走先輩的歐洲之路,向世界講述華工們的傳奇故事,緬懷這段應該被銘刻的歷史。(參與采寫:王歡、王子辰、李永錫)
作者:王陽拍時間 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