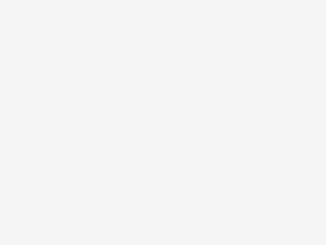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消失」的病人

2月27日,由北京病痛挑戰公益基金會、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舉辦的「吶罕」2018國際罕見病日十周年新聞記者會暨「罕見病醫療援助工程」啟動儀式在北京舉辦。蔣雲生介紹妥瑞氏症。視覺中國供圖

2017年12月25日,在妥友之家的聚會上,蔣雲生正在講述自己的經歷。

病友手中拿著的印有《妥妥的幸福》海報的信封。受訪者供圖
控制的念頭是和痛苦一起到來的。劉亦果每次想要這麼做的時候都會把頭別到一邊,使勁往上翻眼珠,然後哼哧幾下,將身體裡翻騰的氣流壓下去。還有人要跑到沒人的角落,拼命抽搐,甚至「手指變成了掰都掰不動的蘭花指」。
在很多場合,這是避免尷尬的唯一方式。否則,身體就不得不交給那個叫做妥瑞氏症(Tourette Syndrome)的疾病掌管。這種病因未明的精神障礙經常引發抽搐、痙攣等症狀。劉亦果的其他病友中,還有大約15%的人有「穢語癖」的症狀,會不分時間、場合說髒話。「就像大腦中的神經信號失控了」。
在中國內地,沒有妥瑞氏症患者的互助組織或者協會,他們的具體數量也無人知曉。如果按照美國妥瑞氏症協會醫療咨詢委員會主席約翰·沃卡普給出的1‰的發病率,那麼國內至少有超過100萬名成年人遭受著妥瑞氏症的困擾。未成年人的數量則在10倍以上。
只有在極少的情況下,他們才會被人注意到。最近上映的印度電影《嗝嗝老師》講述了一名患有妥瑞氏症的女孩在經歷多次失敗後成為一名老師的故事。一些患者群因為這個電影熱鬧起來,有人特意趕在零點觀看首映,有人連著看好幾遍,寫下長長的影評,還有人發起組團觀影活動。
在此之前,患有妥瑞氏症的導演蔣雲生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叫做《妥妥的幸福》,也引起不少關注。
剩下的大多時候,上百萬妥瑞氏症患者「消失」了。
這些患者需要面臨的不只是身體上的不適,他們還要面對旁人的不解,擺脫一些近似「污名化」的標籤。比如,妥瑞氏症的中文名——抽動穢語症,有時被簡稱為抽動症,這容易讓人想到一種會對別人造成嚴重干擾的疾病。
普通人對這病知之甚少,連找到一個可靠的醫院就診都是一件困難的事。大多數妥瑞氏症患者只能選擇控制自己。
隔離
身體失控的時候,劉亦果經常感到有一股力量,從腰部往肩部迅速上竄,讓她不停聳肩,抽動脖子,發出類似打嗝的聲音。
這位來自湖南的女孩兒8歲時被確診患有抽動症。自此以後,她就一直羨慕別人可以端端正正地站著,自己卻忍不住抽鼻子、動肩膀,「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
小時候,左鄰右舍老是向她家人抱怨,「能不能別讓她老跳霹靂舞。」更惱人的是,她會發出「汪汪」的聲音,一次,街上的一只小狗回應了她,還有小朋友跑過來問,「你能不能別叫了?」
為了避免這樣的尷尬,13歲那年,劉亦果選擇輟學,並在此後兩年拒絕出現在大多公眾場合。偶爾出門時,她的步子快到讓人追不上,講話也更喜歡一個個「反問」句式。她覺得,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行為,「我攻擊你了,你就不會再靠近我。」
她想看書,卻忍不住將書頁撕下來。她想交流,卻和家人頻繁爭吵,為買糖水遲到這樣的小事崩潰。
直到最近幾年,她才選擇走出來。在蔣雲生的紀錄片裡,她出鏡講出自己的故事,還把經歷發表在微信公眾號「妥友之家」上。
這個微信公眾號也是蔣雲生經營的,裡面記錄了患者的各種經歷。一位11歲的孩子1分鐘扭頸62次,被同學戲稱吃了「搖頭丸」。一位大學生在考試時被舉報,監考員判定他的抖動影響了考場秩序。還有年輕女孩因為頻繁挑眉,被誤認為「輕佻」……
但是與患病者數量相比,通過這些管道講述自己經歷的人只是少數。在經營「妥友之家」3年後,蔣雲生認為,最多有1/3的患者,可以接納自己的病情,能向他人坦白的更少。
相比劉亦果少年時期的「自我隔離」,另一些人的隱藏更加「隱秘」。
35歲的張不凡隨身攜帶水杯,在身體失控的前一秒含上一口水。他按照工作安排,調整喝藥時間,以便將有味道的中藥留在家裡。吃飯時,他坐在食堂角落,不和同事一起吃飯、聊天,避免接觸陌生人,就連面對心儀的女孩,也不輕易交往,最多見兩次面,給對方留下「完美印象」。
他獨自一人看完了《嗝嗝老師》,很想在朋友圈分享,但最終沒有點下發送鍵,「怕別人聯想到自己身上」。
來自天南海北的妥瑞氏症患者都在尋找隱藏自己的方法。有人一周紮3次針,幾年下來,身上布滿了上萬個針眼,還有人選擇植入電極,切除小腦片區,換血,往喉帶注入肉毒桿菌……
類似的經歷讓劉亦果絕望,她甚至想過自殺。她記得還有病友發信息給她,「寧願得癌症,少活二三十年都願意,不想像現在這樣活著」。
後來,劉亦果把這種心境,寫成了一首小詩,其中一句寫道:「如果我不在了,這世界不會因此有何改變。世界還在,地球依舊轉,人類還在,人們繼續生活。也許我的家人會傷心,也許我的朋友會沮喪,也許就那麼一兩天或是一兩年,不會再久。」
治療
為了控制自己,劉亦果曾經每天吃掉一大把藥,讓整個人遲鈍到上廁所都不停打瞌睡,「一天睡23小時都會感到的累」。到了晚上,她又翻來覆去睡不著,越強迫自己抽搐得越厲害,喝安眠藥都很難緩解。最多的時候,她喝3種助眠藥物。
她也曾想盡辦法治病。江湖術士告訴她,這病是因為「被蛇精、蛤蟆精嚇到」,媽媽則說「缺鈣、基因不好、沒長完全」。她見過的醫生裡,有的一開口就建議植入50多萬元的進口電極,還有排隊5小時,就診2分鐘,問也不問就一味開藥。
「一查這個病,出來的全是廣告。混亂的治療現狀催生了悲劇。」趙雲清說。她是一名妥瑞氏症患者的母親,從2009年開始,她就用「海夫人」的筆名撰寫相關博文,截止目前,已經分享了近千篇原創文章,還建起了13 個QQ群,將1萬多名患兒家長和患者聚到一起。
她聽過許多混亂的治療經歷。有人為給孩子治病跑遍了全國頂級的神經內科,不停掛號不停換療法,連房子都賣了,可病情還是越來越嚴重,有時連說話都含混不清。還有一個孩子在6歲被確診為抽動症,8歲出現幻聽,9歲被認定為精神分裂,一直在精神病院待到17歲,「真的就從妥瑞氏症變成了精神分裂。」甚至有人從醫生那裡聽到的治療方案是「開顱手術」。
「撞到好醫生,就是撞大運了。」趙雲清感慨。
實際上,資料顯示,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目前的醫學手段只能治療症狀相對輕微的暫時性抽動障礙與慢性抽動障礙,對於表現更為複雜的妥瑞氏症束手無策。
北京市回龍觀醫院心理科主治醫生楊興潔告訴本報記者,當前醫生能做的只是提供一種綜合干預,在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家庭治療、學校教育和飲食調整方面給出建議。通過提早的控制和治療,增加疾病的自愈性。
但自愈率終究幾何?沒有人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一次講座上,沃卡普說,雖然妥瑞氏症的流行程度超乎想像,但面對這種複雜的疾病,現有的科技和能力還遠遠不夠。「至少需要6000個樣本,才能進行初步研究。」
出於大家「想要隱藏」的心態以及臨床試驗和數據分析所要耗費的高昂成本,關於這種複雜神經疾病的研究仍然處於空白狀態。在國內外的學術網站上,大多呈現的也是某位醫生的個案研究或某家醫院的多個案分析。
今年4月,定居倫敦的計算機博士邵明彥,以妥瑞氏症患兒母親的身份,發起了一項針對中國兒童的相關調查。後來,她將這份《2018中國兒童抽動症問卷調查》整理成文,投給了歐洲妥瑞症協會在哥本哈根的學術會議。主辦方采納了這篇論文並鼓勵她開展後續研究,「這是一塊需要發掘的領域,來自中國的數據太少了,也缺乏開展嚴肅研究的學者。」
惡性循環
在一些患者看來,他們被忽略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妥瑞氏症不致命、不傳染,不會帶來迫在眉睫的傷害。這只是「邊緣的」醫學課題,注定無法得到重視和解決。
他們必須接受一種帶著疾病生活的無奈。
張不凡記得,為了求職時在主考官面前表現得正常一些,他面試前在樓道來回踱步,不停抽動、發聲,想讓自己疲憊一些。面試中,他更是不停地告誡自己,「不要眨眼、不要聳肩、不要叫,腦門上有把槍,一抽就一槍打死你。」
他最終獲得了這份工作,但在辦公室的每一秒都過得膽戰心驚。他擔心身上的症狀會在某一刻被同事識破。
這種焦慮再次加重了他的病情,讓他很難再靠「咽炎」一類的說辭進行掩飾。最近他決定辭職,「來年或許會做老板,這樣便沒有人能開除自己。」
「主流觀念認為,妥瑞氏症是一種毛病,通過控制自己,就可以將失控的地方掰回來。」蔣雲生說。
事實並非如此,一位考上醫學院的病友這樣描述「控制自己」的感覺,「我的眼睛緊緊地閉著,有時候能張開一點縫,大多數時候都扭著一片漆黑。我的舌頭時而扭曲伸直到極限,時而死死地向喉嚨縮,使我不能說話不敢呼吸。」
這加劇了單純抽動帶來的痛苦。由於患者想要控制自己,疾病本身又難以馴服,讓他們總結出五花八門的控制方式,又在逐一嘗試後,生出無能無力的念頭。最終,挫敗感滲入生活的每個方面,致使原本受情緒影響較大的疾病加重,也讓患者本人產生強烈的心理對抗,陷入抑鬱、焦慮、強迫的惡性循環。
來自回龍觀醫院的一篇論文顯示,60%的妥瑞氏症患者合併強迫表現,50%合併多動症,此外,患者常常出現焦慮、自傷等情緒和行為問題。
神經疾病被並發的精神疾病複雜化,增加了妥瑞氏症的確診難度,在邵明彥公布的數據中,有50.17%的孩子沒能被確診是何種抽動症。
「我們不知怎麼樣被困住了,也許是因為抽搐是該病的主要特徵,我們從一開始就被抽搐所吸引並去努力探究,因此就忽略了其他的問題,而它們可能比抽搐本身的危害更大。」沃卡普注意到了妥瑞氏症背後的並發症狀。
他在一次演講中展示了PPT裡一幅妥瑞氏症患者的自畫像:那是一個綠色的小人,3個黏結在一起的頭部、頸部表明了他的抽動症狀,更讓人觸動的是小人的表情。沃卡普覺得,「那是比流淚看上去更加沉重的悲傷。」
沃卡普說,大多數患者在15至20歲時,症狀會有所好轉,但在過去6至10年裡,他們會將自己定義為「受妥瑞氏症困擾的人」,這讓他們錯失了一些機會,也影響了他們的正常發展。等到抽搐完全消失,他們也很難擁有「合適的成人的身份」。
在自學多年後,趙雲清概括了妥瑞氏症患者症狀的三個階段:童年時,他們小動作較多,許多人會被當作「多動症」; 青少年時,則會對未來發展、家庭關係、人際交往、戀愛觀產生焦慮,進而出現抑鬱症狀;青年時,她們更多在躁狂與抑鬱之間經歷情緒的「暴漲暴跌」。
「這些心理問題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受婚姻和家庭特徵影響。家庭教養模式、婚姻衝突、家庭成員的社會認知缺陷、社會經濟地位低下、不良的親子關係、缺乏社會支持以及社交孤獨都是影響兒童心理障礙形成的非常重要的變量。」楊興潔和同事有了新發現。
想要走出這重重的困境並不容易。蔣雲生症狀較輕,不會經常發出「引起注意的噪聲」,大專畢業後順利就業,成為一名動畫設計師,在工作中表現出色。
可小時候父親打在他身上的巴掌印,從學前班到中學沒有斷過的中藥針灸,甚至「多動症」的診斷,仍然「梗」在那裡,讓身在辦公室的他每多做一個表情,都會產生「困在潛水艇裡的感覺」。
直到2010年,一次聚會上,有位美國小夥主動問他,「你是不是有妥瑞氏症?」
當天夜裡,蔣雲生看完了一部介紹妥瑞氏症的電影《我是第一名》,提筆寫下一封寄給父親的信。
「在我小的時候,每次我抽動,你都讓我忍,很多人也都叫我忍,輕描淡寫的一個‘忍’字,幾乎充斥著我的童年。說實話,我真的想忍住不動,想成為一個讓你驕傲和開心的孩子,可是每次都讓你更加生氣。這些年,雖然裝作沒事,但我一直在尋找一個答案:我究竟怎麼了?現在我找到了。你沒錯,我也沒錯,錯的只是上帝給我們開了一個玩笑。」
沒多久,父親發來信息,「我不想為過去的一切辯解,天下父母都希望孩子好,我不為自己去嚴厲管教你而後悔,可是我卻為這些年沒有理解你感到抱歉,沒有陪著去尋找病因感到後悔,過去的這麼多年,我們父子一直是僵持的,都沒好好說說話,為此,我想說聲‘對不起’。」
和解
了解疾病,只是與自己和解的第一步。對於不少患者來說,長久以來形成的被排斥、受歧視和羞恥的感覺依舊橫亙在前進的路上。
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2015年蔣雲生萌生了拍攝一部展現國內妥瑞氏症患者生存狀態的紀錄片的想法,並於同年創辦了「妥友之家」。
一開始,沒有人願意成為主角。蔣雲生決定自己出鏡。他找人拍攝了一個2分20秒的「預告片」,呼籲更多妥友「站出來,做自己。」
劉亦果說她是被這句話打動的。「既然大家都嫌我抽起來醜,那我就在電視裡抽給你看。」
還有人在紀錄片裡說,「這個病又不是我與生俱來的,不是我造孽養成的,我為什麼還要因為我的一個先天性的不足或缺陷,去為你們看我的眼神埋單。」
2016年夏天,《妥妥的幸福》在一些視頻網站上線,蔣雲生也陸續將影片和拍攝花絮上傳到了妥友之家。
同為妥瑞氏症患者的上海高中生餘波參加了這部紀錄片的首映儀式。在現場,他決定向身邊的老師同學坦白自己的病情,並將妥瑞氏症作為一個課題進行研究。
整整一學期,他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病友展開交流,又在自己的學校開展了心理實驗與問卷調查。
起初得到的反饋並不樂觀,在受訪的115名同學中,只有少數同學聽說過妥瑞氏症。針對7名志願者的心理實驗顯示,在分別面對正常人和妥瑞氏症患者的交談中,大家對患者的接納程度較低。
第一次調查結束後,餘波為填寫問卷的同學播放了關於妥瑞氏症的視頻、資料。普及後,大家的接納程度明顯提高。7名志願者中有2人表示,願意與妥瑞氏症患者建立伴侶關係。
更讓餘波難忘的是一次談話。在一次晚自習中,同宿舍的一位同學直接走過來跟他說:「你能不能不要發出那種聲音?真的很令人惡心。」餘波掐住自己的脖子度過了自習,其他人對那位同學進行了「聲討」。
回寢室後,那位同學約餘波去陽台聊聊,他告訴餘波,這個環境中,大家會習慣並寬容,但是如果不找個辦法把它控制住,以後必然會遭受很大的問題。
「忍受,只是沒能想出真正能夠解決的辦法。」餘波說,他擁抱了那位同學,體會到另一種感同身受,「就像茨威格筆下,真正的同情。它毫無感傷的色彩,但富有積極的精神。」
自由
上線將近3年後,《妥妥的幸福》的播放量僅有30餘萬,妥友之家的粉絲也停留在4000多個。
與社會主流文化、生活或生存方式的衝突,困擾著很多患者。蔣雲生發起過幾場針對病友的線下活動,但在原本充滿理解、能夠「自由呼吸」的地方,仍然有執著於「控制」自己的妥友,「有人一天吃8片藥,有人對著牆角吐口水,就像鴕鳥一樣,將自己埋在沙子裡。」
「我們的文化講求大同,要大家差不多一模一樣,所以會有槍打出頭鳥的說法,也造成我們對於不合規範的、不合常理的東西的一般處理方式。」趙雲清說。
邵明彥告訴記者,與國內的環境不同,在英國,無論孩子入學還是成人求職,當地的妥瑞氏症協會都能提供一些幫助,盡力爭取他們受教育的平等性、找工作的公平性。而這些國內仍然有所欠缺。
「最大的弊端是我們現在的社會,還沒有教給大家,要去接納不同的人群。」邵明彥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英國,即使孩子症狀很嚴重,也只是偶爾有路人會尋找聲音的來源,隨後會立刻調頭不再看。但回國後,孩子會不斷問她,「媽媽為什麼有人老盯著我看?」
前不久,劉亦果在一個公益組織的支持下,決定在廣州發起一場名為《妥妥的幸福》的音樂會,但在多次發布招募信息後,沒有一位患者主動聯絡她。
僅有的見過面的3位廣州患者全部拒絕了她。有人說不想被別人看到臉,還有人說前兩天兒子散步時,沒控制好抽搐了一下,孩子馬上轉過頭來說,「媽媽,你不要在公共場合這樣蹦躂,太丟人了。」
「妥友之家提倡每位妥友都能成為志願宣傳員,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幾年下來,蔣雲生習慣了大多數妥友想要隱藏的心情,但有時不免無奈,「出門只掃門前雪,難道要讓嚴重的人,這輩子都像這樣躲躲藏藏嗎?」
劉亦果已經決定不再躲藏了。她不再勉強控制自己。病情發作的時候,她會拿出一張白紙,在上邊畫下一條橫線,然後告訴自己,「你的心,要像這個海面一樣平。」
就在看電影《嗝嗝老師》時,她也在影院跟著不停「打嗝」。坐在旁邊的一位老先生提醒她「你深呼吸一下」。她又大聲「嗝」了一下,「沒事,我是妥瑞氏症患者。」
其他人也找到自己和疾病和解的方式。餘波想開展新一輪的調查,張不凡計劃向身邊最親密的10位家人好友坦白自己的病情。
而蔣雲生則計劃繼續拍攝普及妥瑞氏症的影片。他覺得,永遠會有患者從紀錄片裡獲得一些力量。他甚至想好了自己墓志銘上的文字:「一位致力於普及妥瑞氏症的導演,他的作品幫助了很多患者。」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張不凡、餘波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王豪 來源:中國青年報